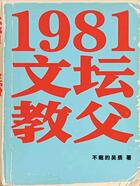
第22章 厂报社
杨百川在厂长办公室门口杵了半分钟,才轻轻叩响了门。
“请进。”女人的声音闷沉沉地传出来。
他将门推开一道缝,侧身挤了进去,脸上浮起笑意,手伸到背后把门掩住。
“小杨啊,啥子事?”
贺萍伏在办公桌上写材料,抬头见是他,微微一笑又埋下头去。
杨百川站在门边不动:“贺厂长,你上回不是说,我写了小说要先拿给你看嘛……”
贺萍又把脑壳扬起来,眼神里带着期许:“你又有新作啦?”
杨百川从挎包里摸出一篇稿子,正是周明远看过的《一个人的中国》光明版。
给贺萍看这篇最中规中矩的,是因为摸不准她的底,不清楚她的文学审美如何。
要是贸然给她那篇《雾镇》,说不定还会坏事,更遑论《潮生》那种探讨经济改革、触及禁忌的小说。
《一个人的中国》是老实巴交的现实主义,故事扎实,读起来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而且这个版本的结尾也是特供的,贺萍挑不出硬伤。
杨百川明白这并非纯粹的文学讨论,还关涉贺萍对他这个人的看法,所以在这些细节上需要倍加小心。
另一方面,他也没安心想让贺萍给他提意见,老实讲,在文学领域,他觉得女人还不够格。这篇稿子不过是一条橄榄枝,让贺萍晓得他杨百川心里记挂着她。
杨百川走过去时,贺萍站了起来,双手接过稿子。
“我还在写一个材料,等空了看哈。”
“厂长你忙你的,啥子时候看都得行,我改天再来请教~”说罢转身要走,被贺萍喊住了。
扭过身去时,女人慢慢地踱步过来,斜倚在办公桌的边沿上。
“小杨,我没记错吧,你是采购科的?”
杨百川点点头。
贺萍摘下眼镜,扯着衣角擦了擦,重又戴上:“你感觉如何嘛?”
这一刻,杨百川忽然有一种学生时代被老师问话的感觉,是那种带着威严的关切。
“还可以,经常跑乡下,还蛮有意思的。”
杨百川想起韩家书让他提调岗的事,组织好的语言却像块秤砣一样坠在喉咙里。开不了口啊。
他有点后悔没带那瓶茅台来了。他和贺萍的关系当然没到那个地步,没点实在东西,咋好意思开口让人帮忙?
他暗骂自己脑壳抽筋,自鸣得意地带篇稿子就来了,实际上0个人稀罕看。
另一方面,他又觉得韩家书把事情想得简单了。就算带了茅台,这种事也难办。
临江县酒厂属于国营企业,在那个年代,他们的正式职工都是有编制的。
穿越前,杨百川虽没在体制内待过,但也知道,在那些受编制约束的单位,换岗没那么容易。
再者,那时候的企业还没开展改革,和各个经济部门联系密切,许多事都得由上级讨论决定。对于人事调动,而且还是跨部门的调动,厂长恐怕很难拍板。
就算是《乔厂长上任记》里那个看似雷厉风行的厂长,也都只管得了生产上的事。
贺萍走过来,像个长辈似的拍了拍他的肩头:“跑外勤风吹日晒的,还是辛苦。”
杨百川笑着客套几句,转身又要走。
贺萍带着笑意的嗓音从身后追上来:“你老是急性子。”
“贺厂长……科室还有事,我先回去了哈。”
贺萍哼地一笑:“小杨啊,我当厂长的,还不清楚你们科室?”
杨百川一愣,尴尬地笑了笑,没搭白。
贺萍又凑近两步,伸手捏住男人的手腕:“你怕我?”
杨百川呆在原地,心里乱七糟八。
这是搞啥子名堂?
这婆娘莫不是想……
忽然冒出个恶狠狠的念头:老子怕你?
反手扣住贺萍的手腕。
他看到那副圆框眼镜后的瞳孔倏然紧缩。
两人都没说话。
贺萍猛地抽回手,在裤腿上蹭了蹭,又转过身,快步走回办公桌。
有了刚才的举动,杨百川心里更稳当了些,那句憋了很久的话冲出嗓子:“贺厂长,能不能给我换个岗。”
贺萍扶着眼镜:“你不是说采购干着还可以吗?”
“我来给你当秘书嘛。”
这念头是临时冒出来的。
他逐渐明白了,贺萍这女人,看着厉害,其实吃硬不吃软。自己强硬一点,说不定能掌握主动权。
贺萍沉默片刻:“你确实更适合文职……秘书我不需要,你去厂报社吧。”
杨百川心里暗喜,这算是意外收获。厂报一个礼拜出一期,要是真能去,不仅可以坐办公室,还有稳定充足的时间写小说。
脸上却依然绷着:“谢谢贺厂长,你忙嘛,我先走了。”这次贺萍没再喊住他。
没有人事调动的公告。杨百川悄无声息地在厂报社有了一个工位。
看来韩家书不是想得太简单,而是深谙潜在的弯弯绕绕。
虽然现下体制森严,厂长的人事任免权也有限,但她能让杨百川编制留在采购科,人去厂报社干活。
厂报社听着像回事,其实就三间办公室。
一间是社长办公室,长期空着,一间由周明远独占,杨百川的工位在剩的那间,和两个同事共用。
也就是说,厂报社其实只有五个人。
另两个同事,一个姓闻,名字叫闻天常,歪号老臭。(“闻”字让人联想到闻味道,一来二去就喊成老臭了。)
另一个叫蒋解放,大伙都喊他老蒋。
老蒋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杨百川到厂报半个月,才第一回跟他讲上话。后来听老臭讲,这姓氏使他在过去的岁月里吃了不少苦头,让他习惯于把自己包裹起来。
厂报的作息是早十晚六,标准的八小时工作制,但老臭经常迟到早退,周明远也从没说过他。
杨百川的新鲜劲只持续了一个多月。整天不是看最新报纸、搜集新闻,就是看职工投来的稿子。虽说不累,但跟下乡采购粮食比起来,枯燥多了。
那些稿子没几篇写得好的。大多连文从字顺都做不到,错别字连篇,主题也比较雷同,要么歌颂时代(有篇制曲车间写的《我为四化养酵母》,通篇二十八个“改革”),要么像流水账一样写自己的工作日记。难怪原身那篇毫无亮点的《遥远的海岛》,也能引起波澜。
杨百川干到第二个月时,也成了老油条,跟老臭一样晚来早走。
某天拎着挎包要溜,刚出门,在楼道撞见个矮墩墩的身影,正是贺萍。
贺萍抬起手腕,看了眼双狮表:“诶,小杨,不是还没到点吗?”
杨百川放下挎包,尴尬地笑笑:“活干完了……”
贺萍也没计较,举起手里的牛皮文件袋,转开封口处的绳子:“小说我看完了,写得很好啊。”
这时,周明远从隔壁办公室过来,蒋解放畏畏缩缩地跟在后面,看来是他去喊的老周。
周明远满脸堆笑,热络络地迎上来,伸出一只手:“哎呀,贺厂长,来视察也不提前说一声!”
贺萍也伸手过去,被周明远双手抓住,甩个不停。
“不是公事。小杨的小说,我看完了,来跟他交流一下。”
周明远感叹:“我们厂报捡到个才子啊!是《一个人的中国》吗?”
贺萍点点头:“你也看过?”
“我之前帮他投市里面的作家联谊会,用的就是这篇嘛!写得好!”
贺萍盯着杨百川,假装板脸:“哎呀,原来是已经成名的作品。小杨,我不是说写好了先拿给我看吗?”
杨百川一愣,讪笑着摸了摸后脑勺说:“我的错我的错,下回一定先拿给厂长审。”
贺萍转头问周明远:“老周,你有没有看出来这个陈德顺是哪个?”
“哪个?没看出来诶。”
杨百川心里暗骂,你个老周,我早跟你说过是老孙,还装。个老滑头,晓得在领导面前要装傻示弱。
贺萍说:“老孙啊,孙德贵。”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像!”周明远夸张地应着,和杨百川对视一眼。
贺萍接过蒋解放递来的茶杯,呷了一口:“我在想啊,老孙一个抗战老兵,天天守门确实不合适。小杨的小说很有想象力,给我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我看,厂报可以搞个采访专栏,报道老兵的事迹。这样才能带动大家,多关心关心这些老同志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