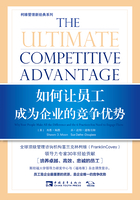
第二章 范式:促使每一个员工转变为领导者
任何组织中积极性最高的人都是领导。
领导是对结果负责的人,无论好坏他们都得“拥有”结果,所以他们竭尽所能去争取最好的结果。领导主动关心目标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其他下属,毕竟下属们不用担责。
东西的主人才会去照看东西,例如洗车、修整房屋、清理花园,人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在乎。另一方面,没有所有权才会无所顾忌,谁会去洗一辆租来的车呢?
在一个组织中,道理也一样。领导是目标、项目、措施、系统的所有者,他们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是让非所有者的其他人去在乎这些东西。但是无论给予下属们多少报酬、承诺、晋升机会,他们都不会像领导那样在乎,下属们不拥有任何东西。
自从第一个组织(不管它是什么组织)诞生之日起,领导们便被这个问题困扰,怎样才能激励员工做到最好?年复一年,专权的领导们除了让员工们感到恐惧,再没有别的结果。 20世纪,科学的管理者们使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恰好适合那些没有教育背景、对工作期望值不高的工人。过了半个世纪左右,发生了一些变化,员工们的教育背景越来越来高,期望值也随之升高,迫使领导们赋予他们更多参与权。“参与式管理”就此兴起,其最初的目的就是消除官僚层级,从而更加民主。
这种方法没有奏效,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层级观念更加尖锐,内部山头林立,地盘战全面展开,领导和下属之间出现政治斗争。即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兴时代,工业时代的层级斗争仍层出不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种心理影响:“我不如你那么重要。”矩阵组织试图弱化这种影响,结果却带来了混乱,组织越复杂,员工感觉越无助。直到2000年,套用某些敏锐观察者的话,出现了这样的思潮:“日趋严重……各个级别的人都很沮丧,讨厌那些毫无意义的层级、傲慢自大的领导、独裁专权的决策、繁文缛节的工作”。
现在,领导们不知所措,迫切地希望找出领导和激励下属的方法:“我是领导还是好朋友?我要成为一个集权的管理者还是放权的管理者?我是X理论管理者,发号施令,看谁是老板,还是Y理论管理者,因势利导,平等待人,善解人意?我是伟大的梦想家,还是温文尔雅的分析者?我是系统论者,还是人本论者?
斯坦福大学哈罗德·李威特教授精妙地描述了领导者们今天的困境:“人本论者重视组织中人的作用,关注人的需求、态度和情感。他们大多反对层级,将层级看作束缚、禁锢,甚至是枷锁。相反,系统论者注重事实、评价和系统,他们大多喜欢层级,认为层级作为有效的结构,可以支撑完成重大事项。人本论者对系统论者的成见是认为他们麻木不仁、固执己见,觉得只要是自己无法衡量的东西就不存在,系统论者则讽刺人本论者头脑发热、情绪激动、思路不清。”
当然,大多数聪明的领导者都徘徊在这些选择之间,渐渐地他们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风格。有些领导尝试平衡“老板”和“好朋友”这两个角色,但这对关系极难平衡。有些领导们摇摆在不同风格之间,对过于激进的员工进行微观管理,却让其他人都感到被忽略了,也开始激进起来,最终,他们也需要微观管理,如此一来,你逃离了一个危机,又陷入了另一个困境。
李威特教授把这种典型的组织领导方式总结成“依赖、怀疑、冲突、谄媚、误解和诸多其他人类的痼疾在侵害着每个大型机构”。
但是,问题不在于如何在两种没有作用的领导方式之间平衡,而在于找到有效的领导范式。
在我们的文化中,领导一般是由职位决定的,但史蒂芬·柯维说:“我并不认为当上了CEO就是领导, CEO并没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像领导。”他的意思是说,权力的授予并不能让你成为领导,一个职位赋予你权力,但不会让你成为领导,就像有了一双雪橇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名滑雪选手一样,一个职位不会自动给予你任何东西。
领导力包含了两层意思:名正言顺的职位和与生俱来的权威。观察一下你所知道的领导,有的人虽身居要职却毫无影响力,有的人确是无冕之王。
实际上,无论他的职位和岗位如何,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领导。甘地带领整个印度民族赢得独立,却没有一官半职。每个组织都是在一个非正式的核心人物网上寻找智慧、建议和方法的,这些人往往既不是官员,也不是管理者,却凭借着经验和影响力赢得了“非正式的权威”。
依照已有经验,让几个领导决定所有的事情会制约整个组织的发展,这并非新闻,但改变这种情况的努力少之又少。嘉里·哈摩尔说过:“我们的组织仍然给予金字塔顶端的人太多权力和权威……我们应该让领导的工作更加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