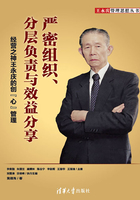
关系企业成长的法制背景及其他
在台湾地区,关系企业诞生在前,而立法在后。当地社会对于如何规制关系企业的呼声由来已久,但因为各方对于如何规范意见不一,有关立法的研修和审议时断时续:先是学术界对关系企业的形成机理和运作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然后是1976年连续爆发了两起关系企业弊案 之后,台湾地区成立了专案小组并参照德国在1965年颁布的“股份公司法”,草拟了“关系企业立法草案”;最后又几经反复,并于1997年在修订“公司法”时增订了“关系企业专章”。至此,台湾社会才算是正式有了针对关系企业的法规条文。
之后,台湾地区成立了专案小组并参照德国在1965年颁布的“股份公司法”,草拟了“关系企业立法草案”;最后又几经反复,并于1997年在修订“公司法”时增订了“关系企业专章”。至此,台湾社会才算是正式有了针对关系企业的法规条文。
有法律学者认为 :“有关关系企业的立法精神基本上汲取了美国法院处理关系企业问题所建立的三原则:①揭穿公司面纱原则,即法人人格的否认。②深石原则(Deep rock doctrine),即子公司资本不足,且为母公司之利益而不按正常方式经营业务者,于子公司支付不能、破产或重整时,母公司对子公司之债权应次于其他债权人受偿。③控制股东之忠实和注意原则,即以德国股份公司法有关事实上的关系企业的规范为主要内容。以上三者构成了台湾现行公司法的规范架构。”
:“有关关系企业的立法精神基本上汲取了美国法院处理关系企业问题所建立的三原则:①揭穿公司面纱原则,即法人人格的否认。②深石原则(Deep rock doctrine),即子公司资本不足,且为母公司之利益而不按正常方式经营业务者,于子公司支付不能、破产或重整时,母公司对子公司之债权应次于其他债权人受偿。③控制股东之忠实和注意原则,即以德国股份公司法有关事实上的关系企业的规范为主要内容。以上三者构成了台湾现行公司法的规范架构。”
尽管有了相关法规条文,但台湾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期间,仍有多达数十家关系企业出现了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司“扩张太快、企业主短视急功近利、借壳上市、做假账制造上市行情、违法吸金冒贷护盘套牢、相互投资交叉持股、虚增资本、董事兼充、内线交易利益输送、掏空公司资金、转投资亏空等 。”这些弊案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规范集团企业的经营行为是一个超级大难题,不仅是台湾,而且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二是消除弊案,或把弊案发生的机率降低到最低程度,仅靠立法不足以完成,另还要依靠企业家的人格特质及其选择和不断强化的企业内部的关系、制度及结构。
。”这些弊案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规范集团企业的经营行为是一个超级大难题,不仅是台湾,而且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二是消除弊案,或把弊案发生的机率降低到最低程度,仅靠立法不足以完成,另还要依靠企业家的人格特质及其选择和不断强化的企业内部的关系、制度及结构。
除立法层面以外,学术界也对关系企业形成的其他法律和经济背景进行了广泛探讨和研究 。有学者认为,关系企业的兴起与台湾缺乏反托拉斯法和实行“奖励投资条例”及其多次修订密切相关。因为反托拉斯法的缺失,使得关系企业能够自由选择最有利的组合方式结合在一起并向大型化发展;奖励投资条例中的税捐减免部分,如“新投资创业之生产事业可享受五年免税”等条款,降低了企业在已有规模框架下增加产能的偏好,转而采取另行成立新公司的方式并倾向于数量化扩充。
。有学者认为,关系企业的兴起与台湾缺乏反托拉斯法和实行“奖励投资条例”及其多次修订密切相关。因为反托拉斯法的缺失,使得关系企业能够自由选择最有利的组合方式结合在一起并向大型化发展;奖励投资条例中的税捐减免部分,如“新投资创业之生产事业可享受五年免税”等条款,降低了企业在已有规模框架下增加产能的偏好,转而采取另行成立新公司的方式并倾向于数量化扩充。
台湾地区“公司法”虽然规定企业可以采用变更原登记营业范围来扩大业务范围,但关系企业发现,变更营业范围的手续通常十分繁杂,且不易获得当局批准,遂更倾向于采用另行成立新公司的办法来解决。也有学者从企业投融资的角度探讨了关系企业兴起的原因,认为在投融资方面,当企业遇到新的投资机会时,通常会相互背书向银行获得贷款。此时,关系企业的负责人会发现,通过多家分子公司分别向银行融资的力度和金额不仅要高于单个企业,而且不需要求助他人。当然,在利润留存或自有资金不足时,关系企业必定会向外寻求新的资金来源。而当内外部资金结合之后,企业负责人往往选择在关系企业框架下另行成立新公司来图谋进一步的扩张。
另有学者则从企业经营管理层面探讨企业结合在一起的动因,认为从管理和竞争的层面看,企业成长至一定规模后,采用多部门独立经营的方式有利于发现和培养高级管理人才,有利于沟通和协调,包括实际业务中的资金调度和周转在内。此外,企业家为应对环境变化,特别是为了分散市场投资风险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从而也在客观上为设立更多的分子公司提供了条件。
“中华征信所”于1978年出版的《台湾地区集团企业研究》一书的总论部分刊登了陈定国教授的文章,认为关系企业在当时不宜采取正式单一法人方式经营。该文实际上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企业家为什么愿意以“非正式”途径设立关系企业的原因。首先,如果企业家选择了“多事业部组织之单一法人之巨型企业”的途径,那么常会“因融资担保不易,累进税率较高,保留盈余受严格限制,税捐人员特别监视,以及社会大众要求较多等”影响到企业的日常经营。其次,如果企业家选择了“控股公司”的途径,那么控股公司只能通过董事会(股权代表)发挥作用,而无法向附属公司直接派遣经营管理人员,再加上台湾地区“公司法”规定,“企业转投资金额不得超过资本额的三分之一”,所以企业常因无法设立更多附属公司而影响到自身成长。再次,如果企业家选择了“母子公司”,那么也有可能会遇到像设立“控股公司”一样的困难和问题。
陈定国教授建议说,在当时的环境下,“真正可以发挥经营管理效率,又可避免融资和税法等不利限制的唯一途径是设立关系企业(Group Company)”。因为在关系企业架构下,各成员企业皆以公司法人形式存在。这样做可使企业的主要关系“不在于法人之间之股本投资,而在于主要股东之私人投资。法人投资和私人投资受公司法的限制程度不同,前者不能创造太多的附属公司或子公司,同时每一转投资行为皆需入账,皆须编制合并报表;而后者却可以创造出很多成员公司,不仅投资活动不必入账,不必编制合并报表,而且企业也可灵活经营,真正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诸多好处”。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许多企业仍沿循着关系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有些企业,特别是台塑关系企业,正是在这一治理结构下成长为一家世界级集团企业的。当然,一个企业的成长总是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条件密切相关。比如日本的财团、美国的控股公司、复合企业、欧洲的辛迪加和卡特尔等等,都是其社会环境演变的综合产物。台湾地区的关系企业也不例外,既有其成长的特殊历史背景,也有其成长的特殊历史条件。
关系企业的“总部组织”至今仍以“超法律” 形式存在,尽管其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分离并不明显,但企业家却总是能透过其顶层设计与操作才能,使各关系企业之间能够形成“利害与共,同属一体”
形式存在,尽管其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分离并不明显,但企业家却总是能透过其顶层设计与操作才能,使各关系企业之间能够形成“利害与共,同属一体” 的关系,并一一化解成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和困难。
的关系,并一一化解成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