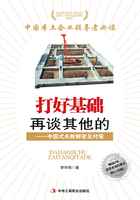
第六节 没有方向的老板
清代“狂生野才”陈澹然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而兴明公司的问题恰恰在于“只谋一域不谋全局,只谋一时不谋万世”。
偌大的公司没有成文、成系统的管理制度体系,如《人事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所有的只是一些如《关于××问题的处理办法》、《关于××的临时规定》或《关于××事宜的决定》之类的“暂行规定”,这些“规定”和“决定”大都不超过一页纸,不超过15条,文件含糊、笼统,各种条文不甚具体,同一条款适合于多种解释。每一个“规定”和“决定”就是一颗珠子,公司有数千颗珠子,却没有一根线把它们串起来,形成一个体系和整体。由于每颗“珠子”都是在不同发展时期根据当时情况而随机制定的,只是为了解决某一个特定问题,并无长远和全局考虑,因此,不同“珠子”的内容相互矛盾,当两个部门为某一问题发生分歧时,每个部门都能在“珠群”中找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一颗来证明对方错了。
唐氏兄弟心中只有“点”,没有“面”、没有“系统”,更没有“方向”,只是被动地被企业每天发生的事情拖着走,比如,今天珠海市消防大队来公司检查出很多问题,就马上下令成立“义务消防队”并制定《消防安全管理暂行规定》;明天有员工到珠海市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公司不与员工签劳动合同、不买工伤保险,就马上开会决定即日起跟全体员工签劳动合同并买工伤保险。所有工作都是“应对式”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非按事先确定的方向主动构建系统性的管理框架。
2014年8月的一天,企划中心总监赵文成找唐明副总裁谈本人2014年年薪及年度考核问题,于是,唐副总裁叫来赵总监的上司、战略中心徐中夫,当场下令由徐中夫制定出《2014年企划中心赵文成年薪及年度考核方案》,这让刚入职的徐中夫一头雾水,为什么高管的“年薪及年度考核方案”不在年初做而要等到8月才开始做?为什么不由人力资源部统一编制全公司高管的《年薪及年度考核方案》,而要由各一级中心自行编制?无奈老板命令已下,只好服从。徐总花费一周时间认真做出《2014年企划中心赵文成年薪及年度考核方案》交给唐副总裁后,却迟迟没有下文,直到11月“战略委员会”作出决定,全体高管2014年度考核只以11月、12月两个月目标达成情况为准,1 ~10月工作成败一律不计入年度考核之中,赵文成也一样。于是,徐总花费一周时间全身心投入做出的考核方案等于一场空。
一天,唐副总裁找来徐中夫,指示他制定一套公司文控中心整顿方案。由于有了上次的教训,徐中夫多了个心眼,将自己前公司的同类电子档文件调出来形成一份《文控中心整顿方案》,换成兴明公司的名,总共用了5分钟时间,一周后交给了唐副总裁。一个月过去了,唐副总裁毫无回馈。一天,徐中夫问:“唐副总,上次我那份《文控中心整顿方案》是不是写得不好?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下一步工作指示?”唐副总裁说:“我看了,写得很好。但现在公司决定新招一名管理者代表,《文控中心整顿方案》还是由新管理者代表来了以后再做,你那份就不要了。”徐中夫听罢只觉得唐副总裁就像一个花花公子,一天之内跟三个女人说“我爱你”,谁如果当真,谁就倒大霉。
奇怪的是,公司里没有一个目标明确、具有决断力的“领头羊”,唐氏兄弟极少给各部门主管清晰的工作方向,大多数时候,公司各部门各行其是、各自为战,步伐绝不统一。如果遇事请示老板,唐氏兄弟的回复往住是告之其通知总裁办,由总裁办召集相关部门主管开个会,在会议上讨论决定,而会议上又是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
由于每次请示老板都无法得到明示,久而久之,各部门主管明白了一个道理,老板是不决策的,决策靠会议,于是,遇事就直接找总裁办,由总裁办召集专门会议讨论。开始时,总裁办秘书还请示一下老板“此会开否?”,后来发现老板一概同意,渐而不再请示老板,而是直接通知老板会议时间。于是,就渐而出现这种情况:唐氏兄弟走进会议室时会常常问一句“今天会议是什么议题?”
久而久之,公司形成了一种“非老板主导文化”,即凡各部门主管通知总裁办召集会议,总裁办一概应允,老板也一概参加。有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上午A部门主持召开了一个主题是向左走的会议,下午B部门又主持召开了一个主题是向右走的会议,两个会议唐氏兄弟都参加,直到两个会议都开完后才发现其中一个会完全可以不开。表面看来,最终的会议决议都是老板拍板,但开什么会、该不该开、什么时候开,则完全不由老板掌控,而是由各自为政的一个群体各自操纵,于是,老板就像大海中的一叶毫无方向的小舟,随着一个又一个左右扑来的巨浪不断调整航向,漫无目标、无休无止。
老板没有方向感,靠会议解决问题,这样,常常会因上一个会议与下一个会议决议不同造成经济损失,于是,再来开一个会议解决这一问题。公司高层靠会议工作,中层和基层也如此效仿,每天各种会议开得轰轰烈烈。由于无人统筹,A单位与B单位往往会就同一个问题分别开会,开完之后又突然发现形成的决议不同,于是就再开一个统一双方意见的会议。一个新主管入职后会发现公司一天都是会议,根本无法做工作;而老主管则习以为常,不就是开会吗?开吧,反正老板也是这样,至于实际工作嘛,明天再说。
如果说大小会议能解决实际问题倒也罢了,实际上,大多数会议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且不说会议通常形不成决议,就是形成了决议也迟迟不动,无法落地到位。每次“战略会议”的决议就是写满一整白板的“原则”、“规划”、“策略”和“路径”,大家用手机拍下来,各自下去实施。但怎么实施?具体计划安排是什么?终极目标是什么?谁主导牵头?什么时间完成?一概未予说明,数月过去,一切原地不动。而“普通会议”也是如此,比如,有人提出应禁止员工在车间门口吸烟,提了半年迟迟不动,无人落实,车间门口每天照样烟雾缭绕;有人提出应每周开个公司级周例会,由老板主持,提了之后迟迟不动,一年一次例会也未开过;2014年7月唐氏兄弟曾在一次会议上决定进行顶层设计改革,要成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委员会,决定半年后仍迟迟不动。
然而,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不动”,而在于“反动”和“乱动”。
2014年10月,“战略委员会”讨论优化公司组织架构,人力资源中心王总经理异想天开地提出“撤销研发中心”,将研发人员分散到企划中心和工艺中心,理由是“公司白领人员太多,机构重叠,应精兵简政、务实灭虚,合并同类性质机构,把更多技术人员充实到生产一线”。战略中心徐中夫竭力反对,理由是“研发中心是企业的龙头,是核心动力机构,是企业创造力的源头,撤销研发中心就等于自毁动力、消灭技术创新”。徐中夫原以为老板会有最基本的理性,但唐氏兄弟偏偏支持“撤销研发中心”的主张。徐中夫惊讶地看到,“言必称战略”的唐氏兄弟居然连“研发是创新之源”这样最基本的战略都不懂,缺乏最最基础的企业管理常识。
徐中夫单独对唐兴总裁说:“研发中心就如一支军队的新武器研究所,撤销了新武器研究所,一国军队就完了,一旦外敌入侵,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
唐兴总裁说:“不要说得那么耸人听闻。我理解你,研发中心本归你管,你是担心撤销之后你在公司分量降低了,所以反对撤销研发中心,你没有站在精兵简政的立场上替公司考虑问题。”
徐中夫明白了,外在表象恰似内在观念,兴明公司基础管理薄弱的表象里面是唐氏兄弟基本管理思想的薄弱。
2014年11月,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兴明公司正式撤销了成立了10年的研发中心,研发总监、产品部经理及一大批技术人员当即离职,公司不再有“研发中心”,如同一个国家不再有新武器研究所一样。唐氏兄弟的私人朋友、兴明公司所有客户及供应商无一理解。
两个月后,珠海市科技局来公司作“科技扶植企业前期调查”,准备为兴明公司提供100万元科技创新无偿资金支持,兴明公司拿不出珠海市科技局要求提供的《兴明公司2015年度新产品开发计划书》和《兴明公司2014年研发队伍情况报告书》, 100万元无偿支持资金瞬间永远飞走;2015年2月,一家德国企业选定兴明公司为自己在中国的研发、生产基地,前来珠海考察时却发现兴明公司只有生产能力,没有研发能力,连研发机构也没有,于是放弃了与之合作的计划,转而与兴明公司的竞争对手×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2015年5月,大梦方醒的唐氏兄弟决定恢复研发中心,打电话请已离职的前研发总监和产品部经理回来,无奈两人已双双在竞争对手×公司就职,不愿意再回来。财务中心韩总经理作了一个计算:“撤销研发中心”事件折腾一圈下来,兴明公司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金额为2000万元。用唐兴董事长自己的话来说,“钱也没了,人也没了,这事是2014年公司最大的蚀本生意,怪不得别人,是自己没事找事。”
唐氏兄弟“只谋一域不谋全局,只谋一时不谋万世”,思维中只有“点”,没有“面”;只有“现在”,没有“将来”;没有系统、整体、宏观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尤其可悲的是,没有最基础的企业管理观念,完全不知孰是孰非、孰对孰错。碰到具体事务,首先就启动小镇农民的固有思维,田地干旱了就放点水,庄稼有了害虫就喷点农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麦子一割,万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