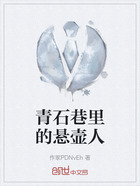
第6章 脉韵中的四季辨证
清明过后,山雨裹着新泥的气息漫进马山镇。王砚在药圃里移栽黄芪苗,指尖沾着的泥土还带着晨露的凉意。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卫生院走廊里候诊的队伍排得老长,大多是捂着喉咙、流着清涕的村民。
“王大夫,我这嗓子又疼起来了。“杂货店的赵婶推门而入,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这次吃黄连上清片也不管用,夜里咳得睡不着觉。“她伸出舌头,舌质淡白、舌苔却黄腻,手心滚烫,后背却裹着厚厚的棉袄直打哆嗦。
王砚刚要把脉,张院长抱着一摞旧报纸走进来,报纸边角用红笔圈着关于流感的报道。“最近寒热错杂的病例特别多。“老人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落在赵婶身上,“记住,春天阳气生发,外寒束表,郁而化热,不能单纯清热。“
他转身从书架上取下布满批注的《景岳全书》,泛黄的书页在春风中翻动:“阴阳为八纲之总纲,表里寒热虚实,要像拆毛线团一样细细分辨。“王砚翻开自己的笔记,父亲用毛笔写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几个大字跃然纸上。
“赵婶这是表寒里热证。“王砚写下麻杏石甘汤合桂枝汤的化裁方,“麻黄解表散寒,石膏清里热,再用生姜、大枣调和营卫。“他特意叮嘱:“药要温服,喝完盖被子发发汗。“赵婶接过药方时,粗糙的手指擦过他的手背,烫得惊人。
深夜,王砚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村尾的李大爷高热惊厥,牙关紧闭。他抓起急救箱冲出门,雨丝打在脸上生疼。急诊室里,张院长已经在准备安宫牛黄丸,见他进来,指了指李大爷青紫的指甲:“真寒假热,仔细分辨。“
王砚颤抖着搭上李大爷的脉,脉象浮大无根,重按空虚。他想起父亲讲过的“阴极似阳“,果断改用白通汤加猪胆汁反佐。当滚烫的药汁缓缓灌入李大爷口中时,窗外惊雷炸响,暴雨倾盆而下。
天快亮时,李大爷终于转醒。王砚瘫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渐亮的天色。药圃里的薄荷被雨水打得东倒西歪,却依然散发着清新的香气。张院长递来一碗姜汤,碗沿飘着两片紫苏叶:“八纲辨证,说起来简单,用起来却像走钢丝。“
他翻开一本油印的《马山四季医案》,里面夹着泛黄的病历纸,记录着历年春季多发病的诊疗经验。王砚的目光停在父亲二十年前的批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医者用药亦当应时而变。“
晨光穿透云层时,王砚在新的病历本上写道:“八纲如罗盘,指引治病方向;四季似经纬,织就诊疗脉络。唯有将辨证融入草木生长的韵律,方能在青石路上走出真正的中医之道。“窗外,山雾渐散,第一缕阳光洒在药圃的黄芪苗上,叶片上的雨珠折射出七彩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