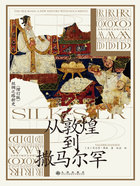
原始史料
8 1901年的尼雅遗址[102]
斯坦因从驮夫手中得到了两块木板文书,他受此吸引,于1901年1月第一次来到尼雅遗址。他注意到此处地形和房屋有什么特征?什么让他最感兴趣?
低沙地上露出古老果树枯萎的树干。向北行约3千米,不久我便看到了两座“老房子”……一番快速调查之后,我发现这些建筑物的建筑模式大体上与丹丹乌里克[103]的房屋相同,只是规模更大,木构件也更为精致坚固。因此我自然得出结论——这些遗迹要古老得多。这也立即得到了证实:在N. Ⅲ遗址的一间外室中,积沙只有约15厘米深,一些雕刻精美的木构件散落在地,其装饰图案无疑具有犍陀罗风格。……再向北行约3千米,翻过宽广的沙丘,我来到一处阿卜杜拉曾在克里雅说起并称之为“炮台”的土坯建筑遗迹。和我猜想的一样,这是一座小佛塔[104]的遗迹,大部分埋在一座锥形高沙丘的斜坡下。
为了方便调查分散在各处的遗址,我将营地扎在建筑群中心。营地周边的地面显露出过度侵蚀的典型特征。大片裸露的黄土上散落着大量碎陶片、倒下的杨树和其他果树那发白扭曲的树干,以及许多一抬起就碎裂的古代朽木。至于这些木料曾所属的建筑,连最粗略的轮廓也不可能找到了。
…………
在这些古代房屋无言注视下就寝的第一个晚上,我却主要在想,易卜拉欣说他一年前“探访”遗迹时看到的那些珍贵木板文书还有多少等着被发现。
1月28日黎明,气温仍远在-18℃以下,我匆匆赶往易卜拉欣一年前捡到佉卢文木板的遗迹。据他所述,他将大量木板留在了原地。我已不可能对他隐瞒我对这些文书价值的判断,后来他似乎后悔当时没拿走一大堆,所以在途中我让易卜拉欣·阿克洪看着他,以防他逃跑或干扰现场。易卜拉欣·阿克洪是克里雅按办[105]派来为我服务的,是一位出色的听差。
前往遗址的路上,期待与怀疑交织的心情很快变成了得到确认后的欢喜。在营地以东近2千米处,我看到了易卜拉欣要带我们去的遗迹……它在一块高出周围被风蚀的地面3.5米到4.5米的小台地上。我走上台地西坡……立刻就在大片的木料残迹间捡到了三块写有佉卢文的木板。这些木料残迹标志着已被完全侵蚀的建筑物构件。到达台地顶部后,我欣喜地发现更多的木板散落在附近几间房屋中的沙子里。凭借残存的墙壁,房屋轮廓尚可辨认。这些木板自一年前被易卜拉欣扔在这里之后,上面又覆盖了一层流沙。但这层流沙很薄,几乎不足以保护最上层的木板免受雪的侵蚀。背阴处的积雪有2厘米到3厘米厚,这毫无疑问就是八天前我从克里雅来尼雅路上遇到的那场雪。
看到自己的话得到证实,我许诺给他的丰厚报酬也有了保证,易卜拉欣几乎快跟我一样开心了。他马上向我指出,木板的发现地并不是这个房间(这里只是他由于完全不知其价值而将其扔掉的地方),而是东边隔壁N. Ⅰ遗址的南角。在壁炉(暴露在沙子外面,很好辨认)和墙壁之间,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约1.2米宽。他用手挖沙寻“宝”时曾在这儿找到一堆木板。这些木板原本是按规律排列,并平放在沿房间那一侧伸出来的矮土台上的,但因为妨碍他挖土,迅速被他扔过断墙,落到隔壁房间里去了。真是万幸,在他发现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就来到了这个遗址。因为这些薄木板现在完全暴露在风吹日晒之中,不可能像之前几个世纪安全地埋在沙子下面那样,能长久保持其字迹清晰如初。事实上,一年的日晒和雨雪,无论多小的量,已经足够使最上面的木板完全暴露在外的字迹掉色——部分文字已经看不到了。
我在散落着易卜拉欣扔的木板的那个房间安排了一个守卫,以防遭到进一步破坏或偷窃,然后让工人们清理他发现木板的N.Ⅰ遗址。这项工作很容易,因为该室只有4米宽、5米长,积沙不深。房屋西北边靠近风蚀斜坡的边缘,积沙仅约半米厚,到了里面增至约1.2米,因为保存较好的东南壁挡住了流沙。……构成房屋地基的是一根根剖面呈方形的白杨木,每根都贯穿几个房间,有些长度超过12米。方木的厚度在15厘米至25厘米之间,根据其所承受墙壁的大小与重要性而有所不同。这些方木完美的加工和装配总让我的工人们对古代木匠的技艺惊叹不已。在这种地基上立着10厘米到15厘米见方的木柱,既支撑房顶,也构成墙壁的框架。立柱之间还有些较小但同样精美的中间柱。柱子平均分布,一般相隔约30厘米,通过屋顶大梁和柱间小梁连成一体。……在这种框架上,一般在较小的中间柱外侧装上一种用红柳枝编的结实的斜纹席,再在框架内外两侧涂上白灰泥构成墙壁。不同建筑物的墙壁总厚度不同,大致在15厘米到20厘米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