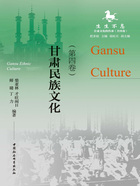
第二节 文明的交流对话与甘肃世居少数民族
一 张骞出使西域
汉武帝为了解西域,曾先后两次派张骞通过甘肃出使西域,并倾国力向今新疆及其以西的中亚、西亚等地区发展。汉代初期匈奴不仅占据整个河西走廊,而且势力一直发展到西域诸国,由西边日逐王统治天山南北的30多个城邦国家。日逐王设置“童仆都尉”常驻焉耆、危须(今博斯腾湖北)、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31],对西域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匈奴的统治阶级和贵族们,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经常侵犯汉王朝的边境,进行烧杀掠夺,掠夺范围甚至达到了长安和甘泉地域。被战火波及的西域民族和中原人民苦不堪言,惶惶不可终日。并且匈奴的掠夺活动基本上中止了中原和西域的商贸联系,严重破坏了中西部的交通要道。
甘肃西部武威、张掖、酒泉等地位于河西走廊,亦即狭义上的河西地区。这一地区是东西长约一千公里、南北宽几公里至一百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南北则两山(南为祁连山,北有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夹峙,形同走廊,故又称“河西走廊”。汉王朝西邻的匈奴和西羌虎视眈眈,对汉王朝的西部边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匈奴控制西域和西羌后,形成了一只强有力的“右臂”,不断地侵扰西汉边境。汉武帝即位后,客观分析西北地区的形势,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这就是所谓的“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在决定对匈奴发动战争之前,首先争取与西域各国结盟,以孤立匈奴,并隔断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汉武帝打通西域,主要目的即在于此。同时,汉朝国内经济发展,商业繁荣,在客观上要求开通对西域贸易的商路。张骞就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出使西域,开通联系中西交往的丝绸之路的。
面对强大的匈奴,汉武帝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公元前140年,当汉武帝听到“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32]的消息后,认为对匈奴进行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汉朝可以联络被匈奴赶走的大月氏,进攻匈奴的右翼,然后集中大军从正面发动进攻,制服匈奴。他决定派遣使臣去西域联络大月氏,当时去西域,在出陇西郡(治地在今临洮)后,必须经过河西走廊,而该地区却被匈奴占据,这就要求必须选择一位特别机智勇敢的人才能完成这一重大使命。汉武帝公开“募能使者”,今陕西省城固县人张骞(约前164年—前114年)脱颖而出,应募出使。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带领100多人的使团,第一次出使西域。张骞从陇西郡出发后,行至祁连山脉附近不幸被匈奴俘获。受俘期间,匈奴单于逼迫张骞迎娶匈奴女人,并与之生下了孩子,即使是这般屈辱也未曾使张骞忘记自己身为“汉臣”的责任。在公元前129年,张骞与其随从堂邑父趁乱逃跑,经过车师国、龟兹国、疏勒国等地,逃至大宛。大宛王热情的接待了他们并派人做向导,帮助张骞最终到达月氏人所在地的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但月氏人疲于战争、西迁家园、休养生息,月氏王拒绝了汉王朝的军事联盟之意。张骞他们在途中看到了汗血马,在临近的大夏国,看到了当地人称为来自身毒(印度)的四川邛竹杖、蜀布等。表面上看张骞的任务失败了,但他对一路的所见所闻事无巨细的做了详细的记录。
前128年,张骞搜集了丝绸之路腹地的大量资料后启程回国。张骞为了不被匈奴再次俘虏,特意从昆仑山北麓行进,经过莎车、于阗、鄯善等地后,终于抵达了中原地区。然而,不幸的是张骞虽然逃过了匈奴的魔爪,却被匈奴的同盟羌俘获。公元前126年,张骞带领其随从堂邑父趁单于病逝,逃离了魔爪。他们跋涉于沙漠、戈壁、冰天雪地之中,以射猎飞禽走兽为食物,历尽艰险,行程万里,终于回到汉朝。前后历时13年,出发时的100余人,归来时只有他和堂邑父两人,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
张骞虽然没有完成和大月氏结盟、共同攻击匈奴的目的,但“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33],了解到有关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风俗、民情等情况,为汉朝了解外部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口。他开拓的主要在天山南麓的线路,就是今日的丝绸之路中线。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汉将卫青大败匈奴,将匈奴赶到黄河以北,汉朝控制了今黄河河套以南地区。元朔六年(前123年),张骞以校尉身份“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拜霍去病为大将,出击匈奴。匈奴浑邪王不敌,从此汉朝对河西走廊实现了完全控制。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次派霍去病迎战匈奴,并派卫青从另一路出击匈奴,匈奴两面受敌,溃不成军,逃至漠北一带后,便再无力南犯汉朝领土。
汉武帝再次召见张骞,询问西域形势。张骞在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得知居住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原来世居河西,与匈奴有矛盾,因不肯侍奉匈奴,故匈奴派兵攻打,未能获胜,从此结怨更深。张骞向武帝建议,要彻底击溃匈奴贵族势力,必须利用乌孙与匈奴的矛盾,与乌孙结成抗匈同盟,“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于是汉武帝决定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与乌孙结成同盟。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封张骞为中郎将。张骞带领300名副使和随从、马匹约600、万数牛羊以及金帛,浩浩荡荡地经河西穿过白龙堆(今敦煌以西),再向西北经焉耆、龟兹,顺利到达乌孙的赤谷城(今吉尔吉斯坦伊什特克城)。
张骞到乌孙赤谷城后,得知乌孙内部已一分为三,加之不了解汉朝,拒绝了汉朝联盟的计划,但表示愿意与汉朝建立关系。当张骞返回时,“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与张骞一起返汉致谢。并且张骞在出使期间,还派遣了许多使节分别出使安息、月氏、康居、大宛、身毒等国家,使节们不辱使命,与各国使臣纷纷返汉致谢。
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中西陆路交通的丝绸之路,为中国和中亚各国及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了新纪元。[34]
二 列“四郡”、据“两关”及汉长城的修建
汉初,匈奴不断南侵,严重威胁边郡社会经济的发展,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朝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大将军卫青出云中击匈奴,夺取河南地。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出陇西,过焉支山,深入匈奴千余里,大败浑邪王及休屠王,匈奴退出河西,河西从此归入汉朝版图。《汉书·西域传》记:“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其后骠骑将军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甘肃永登)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
随着河西四郡的建立,汉在河西修筑了从令居到敦煌的长城要塞,东西长达500多公里。同时还沿长城设置“亭障”“烽燧”,派大批戍卒驻守。士兵的驻守也保证了延长城往来商队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关隘的设置也是汉朝对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贸易保障和管理机制。
河西四郡的建立及河西防务的强化是我国中西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中西交通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河西就已是中原与西域民间交通的必经通道,公元前5至前4世纪,希腊人就已经知道中国丝绸。只是由于匈奴占据河西之后才被隔断。汉在河西的行政、军事设置,将这条古老的民间交流通道官方化,无疑对丝绸之路商道的畅通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35]
三 丝绸之路以及路上的文明
汉代敦煌,是中西交通的枢纽。由敦煌出发至楼兰,再向西分两道:南道缘昆仑山北麓至和田;北道缘天山南路至疏勒,再自疏勒向西南越葱岭经大月氏、大夏可至安息。这是自汉武帝以后,贩丝商队所走的主要大道。当时,自疏勒西北行,经大宛、康居还可到奄蔡。另外,自敦煌出发西北行也分两道:一自天山南路西走,会合北道至疏勒;一缘天山北路西去,也可至大宛、康居。敦煌作为汉代西北的国际交通中心,对中国和西方都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自丝绸之路开通之后,西域之物源源不断传入中国,除著名的大宛马以外,苜蓿、葡萄、石榴、胡桃、胡豆等物都是由此传入;西域音乐、乐器及舞蹈艺术为我国的音乐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尤其是佛教哲学、艺术的传入,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至今仍然存在的深远影响。
丝绸之路的开通,给中国的丝织品大规模的向西输出创造了条件。百人商队络绎不绝的行经河西走廊,之后再由西域转运至中亚及欧洲;安息一些商人就专门从事转运中国丝绸的贸易活动。随着商队西去,中国的生产技术以及思想文化也传向西方并对西方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助进作用,如蚕丝技术、冶炼技术、凿井技术。丝绸之路商贸的繁荣,同时带动了沿途城市采掘与冶炼业、建筑业、纺织业、木器业、制陶业、酿造业、园艺业、玉石加工业、漆器业、造纸业、酿造业、制糖业、粮食加工业、皮革业、药材业等各行各业的极大发展。[36]
丝绸之路的官方化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当时它东面的起点是长安(今西安),经陇西郡(今临洮)西行,然后通过河西走廊,在玉门关或阳关出甘肃。
隋唐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使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埠和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基地,极大的带动了甘肃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唐朝中后期,由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和吐蕃的崛起,导致丝绸之路时断时续,至唐末、五代,丝路贸易日趋衰落,这条路上的繁华也渐渐消退。北宋时期,罗盘的发明促进了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逐渐由陆路向海道转移,但陆上交通也并未消失。公元1014年,西夏攻占西凉后,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丝绸之路向南转移,经由祁连山南麓向西,史称青塘道或南丝绸之路。
习惯上,甘肃省境内的丝绸之路常被分为陇西段与河西段。
陇西段北线由西汉国都长安(西安)出发到咸阳,沿渭河经凤翔、虢县(宝鸡),过汧县(陇县),翻越六盘山,北上原州(固原),沿乌水(今清水河)经石门关(须弥山下),折向西北,在今靖远县石门川索桥古渡处或鹯阴渡口渡黄河,经媪围,沿着腾格里沙漠边缘到达武威。以此道为轴,还有两条通道:一条从唐长安至陇州(陇县)后,沿陇山东麓过今华亭县,至宁夏泾源,过制胜关,越六盘山,达兰州;一条由咸阳到今甘肃宁县后,沿茹河进入固原,在靖远或景泰渡过黄河,向西北至景泰,再到武威。
陇西段中线开辟时间为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平襄县(今通渭)设天水郡时,这条路从长安沿渭河过陇关(后称大震关),翻越陇山,经张家川、陇城(秦安北)、通渭、定西、榆中、兰州,在金城关(在今兰州市白塔山)渡过黄河,溯庄浪河,再经永登越乌鞘岭抵达武威。汉代,北有匈奴,南有羌氐,陇西段中线最安全,而且补给较为充足,是汉代重要的军事运输线和商道,后来成为主要干线。
陇西段南线,从唐长安到陇县,出陇关,翻越陇山,在张家川马鹿镇向南,经清水县,过上邽天水,沿着渭河向西行,经过甘谷、武山、陇西、渭源、抵临洮,渡过洮河,再经过临夏,于永靖过黄河,出积石山,经陇右节度使治地鄯州(今青海乐都)到鄯城(今西宁),越祁连山大斗拔谷(扁都口)到张掖。这条路开通于西汉,兴盛于隋唐,石板路至今尚存。丝绸之路陇西段过黄河后逐渐汇聚成一条主要通道,这就是丝绸之路河西段。丝绸之路沿河西走廊依次经过凉州(武威)、永昌、山丹到达甘州(张掖)。然后,由甘州西行到肃州(酒泉),再由酒泉往西出嘉峪关,经过玉门镇、瓜州到达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沙州(敦煌)。
另外,丝绸之路河西段还有一条重要支线,即由张掖或酒泉沿黑河到居延,汉代时沿途设有肩水都尉府和肩水金关,也可以由敦煌南下青海。
实际上,前面所述各条路线在保持基本走向与框架的前提下,往往是纵横交错、变化不断的。如在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丝绸之路河南道之形成、变迁及所处地理位置,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丝绸之路河南道,是一条以从若羌、敦煌或凉州(武威)出发,经过柴达木盆地、青海湖至黄河以南的吐谷浑地区后抵达长江上游的松潘地区,继而沿岷江而下到古代益州(成都)、建康(南京)为主要线路的国际通道。
这条路线在甘肃省境内有三段:第一段是由松潘出发,沿东岷江而上经四川南坪至文县的阴平南支道;第二段是由文县出发,经峰迭、华严诸古城到迭部的阴平中支道西段;第三段是由迭部出发,经碌曲、夏河、临夏到西宁的河南中支道。
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南北方并不统一,北方的东西部也时分时合。丝绸之路河南道在些时才被正式开辟出来并成为主要干道。然而,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住于青海湟水流域的戎羌民族与甘南居民就在这条道路进行着原始民间往来贸易,甘南至青海商业通道的雏形初步形成,一直延续到四世纪初的前凉时期。
西晋政权覆灭后,群雄割据,张轨控制了新疆东部、青海大部分地区以及河西走廊,并且在甘肃武威建立了前凉政权。丝绸之路在中西贸易中逐渐成形。后来,前凉政权也覆灭后,吐谷浑在今河南地区建立起“河南国”。所以这条道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日也称其为“青海道”。据考证,东晋、南朝、前凉、吐谷浑、柔然、丁零、突厥、铁勒以及西域、中亚、西亚许多古代国家的旅行者多行经此道。
丝绸之路河南道甘南段对西北、西南和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其路沿岷江和白龙江河谷西行过大夏河或黄河干道河谷,由东南向西北斜穿甘南全境。以此路连通四川、青海,它在甘肃境内不仅连接沙漠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也与唐蕃古道交汇于此。
唐蕃古道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东段西行,过咸阳,越陇山,经甘肃天水、陇西、临洮至临夏,在今炳灵寺或积石山的大河家渡黄河,进入青海民和,经古鄯、乐都、西宁、湟源等地,最后到达西藏的拉萨。这条全长3000余公里,跨越世界屋脊的路连通了我国与西南的友好邻邦。
丝绸之路河南道与唐蕃古道在甘肃南部交汇,把中国的中原、江南、西南与沿途西部各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进而贯通中国与中亚、欧洲及印度、尼泊尔等南亚诸国的联系。北宋时,西夏切断了河西走廊。唃厮啰为“联宋抗夏”,在甘肃、青海开辟了南丝绸之路,并保证丝绸之路南线畅通无阻,该线成为宋代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
丝绸之路在甘肃境内,至今保存着众多的石窟、古桥、渡口、险塞、关隘、古城、驿站和大型墓葬群等中西文化交流的遗址、遗物,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整个丝绸之路文化发展的缩影。[37]
四 历史上甘肃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4—5世纪,中原迭经战乱,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破坏;而甘肃河西地区却出现了灿烂的“五凉文化”。其为十六国时期建立在甘肃西部的五个割据政权,它们分别是汉族张氏建立的前凉、氐族吕氏建立的后凉、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汉族李氏建立的西凉和匈奴沮渠氏建立的北凉。在五凉时期的河西地区发端并保存,在北魏时期传入中原并在唐代得以发扬光大的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是“五凉文化”。
虽然后凉的建立者吕光生于氐、南凉的建立者秃发乌孤生于鲜卑、北凉的建立者沮渠蒙逊生于匈奴,但由于长期生活在汉族文化圈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汉化,且钦慕华风。其中,沮渠蒙逊尤为突出,并素著人望。《晋书·沮渠蒙逊载记》称他“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外”,是一位文武全才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与沮渠蒙逊的才智相比,吕光和秃发乌孤要逊色得多,然而他们也懂得用兴理文教来争正朔的道理,身边常有一批汉族士人为他们经邦论道。因此,纵然后凉和南凉时期学风不盛,但也微波荡漾,重文兴教,时而受到重视。
后凉(公元386—403年)为吕光所建。吕光,氐族,略阳(今秦安)人,“世为氐酋豪”。吕光原为前秦骁骑将军,后出征西域,使西域30余国先后归附前秦。吕光从西域归来途中,正值“淝水之战”苻坚失败之时,遂乘机击败前秦凉州刺史梁熙而自立。公元386年自称凉王,号酒泉公,因也建都姑臧,故史称后凉。吕光传位其子绍,后传至吕隆,在公元403年被后秦所吞并。
南凉(公元397—414年)为河西鲜卑族领袖秃发乌孤所建,都西平(今青海西宁),后迁乐都。秃发乌孤建国后,对外采取东和西秦、北结北凉的政策,以图国盛。但乌孤不幸于公元399年醉酒坠马身亡。其弟利鹿孤继位,后又传位其子傉檀。至公元414年为西秦所亡。
北凉(公元401—439年)为沮渠蒙逊所建。沮渠蒙逊为卢水胡族,临松(今张掖)卢水人,博涉群史,颇有雄才大略。他重视文化,爱惜人才;严于法治,法不避亲;注重发展农业生产,使北凉国力很快强盛起来。在此基础上,沮渠蒙逊向四方扩张,从公元411年东占姑臧,到公元421年灭西凉,占有了全部河西走廊。沮渠蒙逊死后,子沮渠茂虔继位。公元439年被北魏所统一。[38]
西羌在秦时南迁到武都地区,被称为“参狼羌”。其中的一支,因聚居于宕昌城(故城在今宕昌县东南)而称宕昌羌。西晋末年,宕昌羌已经形成了个大的部落集团。当时,“有梁勒者,世为酋帅,得羌豪心,乃自称王焉”。至梁勒之孙梁弥忽时,通使北魏,正式建立宕昌国政权。其界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带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辖区大约包括今临潭、岷县南部至天水西界和武都北界一带。宕昌国自弥忽至仚定,共9世。保定五年(公元565年),北周武帝派大将军田弘率军打败了宕昌国,改其地为宕州,兼置宕昌郡。
邓至国亦由羌部落组成,这些羌族,因分布在白水流域,故称白水羌。据《周书》记载:“有像舒治(一作像舒彭),世为白水酋帅,自称王焉。”其辖区大致包括今天蜀陇间的白水江上游南北以及岷江上游诸地。邓至国的风俗物产、服饰等与宕昌国相近。邓至国自像舒治建国,至檐桁,共11世,约七八十年。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邓至王檐桁失国奔长安,宇文泰派兵将他送回邓至。当时邓至以西诸地仍被吐谷浑占据。北周时,在邓至各地建置了郡县。
甘肃的西汉水和白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氐族分布的中心。这里山川险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其中有仇池山,地处甘、川、陕三省交界。《水经注》云:“仇池绝壁,峭峙险,登高望之,形若覆壶,高二十余里,羊肠盘道,三十六回。上有平田百顷,煮土为盐,因以百顷为号。”当中原因战乱分裂之际,氐族酋豪杨氏先后在此建立了五个地方政权,它们是:前仇池国(公元296—371年)、后仇池国(公元386—443年)、武都国(公元447—477年)、武兴国(公元478—553年)、阴平国(公元477—580年)。
吐谷浑自漠北迁徙西北后,至吐谷浑之孙叶延时(约公元319年)始建政权。传六世至阿豺,“自号骠骑将军、沙州刺史……兼并羌、氐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从此,吐谷浑国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成为西北地区举足轻重的强国。
公元490年,伏连筹继吐谷浑王位。“内修职贡,外并戎狄,塞表之中,号为强富。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称制诸国,以自夸大。”吐谷浑国达到鼎盛时期,势力扩展到了今新疆东部鄯善、且末一带。伏连筹死,子夸吕继位,始自号可汗,居伏俟城。隋朝几次发兵打败了吐谷浑,吐谷浑国始由盛转衰。至唐太宗时,由于吐谷浑侵优西北边境,诏李靖、侯君集征讨,杀其王伏允,另立诺曷钵为可汗。公元663年,吐谷浑为吐蕃所亡。
西迁的3支回鹘,先后建立了高昌回鹘汗国、喀喇汗王朝和甘州回鹘汗国。甘州回鹘自唐末建立政权,历五代至北宋,逐渐发展壮大,公元11世纪初,进入鼎盛时期。甘州回鹘汗国政权存在近200年,前后共传10个可汗。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西夏李元昊领兵攻陷甘州,甘州回鹘政权遂亡。
甘州回鹘汗国是游牧的、分散的军事联盟。虽然在甘州设有牙帐作为政权中心,但各地自立酋长,不相统属,分散而牧,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甘州回鹘汗国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以甥舅互称。唐、五代及宋,都有公主与甘州回鹘汗国可汗联姻,甘州回鹘也经常遣使朝贡中原王朝。甘州回鹘汗国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它不仅和西域各国交换频繁,而且与西方的波斯、天竺、大秦都有间接或直接的商业交往。甘州回鹘进入河西走廊后,逐渐学会了农耕,进入了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其生活方式也从游牧逐渐走向定居。
西夏为党项羌的拓跋部所建。唐初,党项首领拓跋赤辞率部归附于唐,唐封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之后,经唐末拓跋思恭,至宋初李(拓跋)继捧,基本上与中原王朝保持友好关系。后传位至李继迁,不断扩张,使贺兰山以西、陇山内外诸族不下数十万帐“无不帖服”,并攻下灵州和西凉府,成为雄踞一方的割据势力。
公元1038年,李元昊仿汉制,自称皇帝,取名大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其地因位于宋之西北,故称西夏。
西夏官制,多与宋同。中央设置中书省和枢密院,分掌文武,下设16司。地方设立州郡。在军事编制上,西夏保留党项人的传统,设置12监军司。
西夏强盛时,其“境土二万余里”,全国分为22州。境内居民除党项人和汉人之外,还有吐蕃人、回鹘人、塔塔尔人等。汉人主要从事农耕,党项、回鹘、吐蕃人主要从事畜牧。西夏畜牧业相当发达,同时重视兴修水利,农业也较发达。境内产盐,手工业有铁矿开采。对外贸易兴盛,“商贩如织”,并有西夏货币。
西夏文化随着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而发展。李元昊创造西夏文字,其文字与契丹、女真字相仿,一字一音,共有6000多字。重视教育,设立“番学”。西夏大量吸收汉族封建文化,也使用汉字、汉语,重视儒学教育。信仰佛教,修建佛寺。
李元昊死后,西夏国势由盛转衰,国内权力斗争加剧,最后在公元1227年为蒙古汗国所统一。西夏自李元昊称帝,直至覆灭,共历10主,190余年。[39]
今甘肃兰州在西晋之后先后出现过几个割据政权,例如匈奴族的前赵、羯族的后赵、氐族的前秦,以及甘肃东部武都地区氐人建立的仇池国。
南北朝时期是甘肃发展史的一个独特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是汉、鲜卑、氐羌、柔然等族互相影响,民族继续融合。南北朝之际,甘肃各兄弟民族由于世代杂居,融合程度进一步深化,到隋唐时,原甘肃境内主要地区纷繁复杂的兄弟民族基本上融为一体。各割据政权处于较低的经济文化发展阶段,从而产生了频繁的掠夺性战争,以财富、土地和人口为直接目标。战争和大规模的强迫性移民,虽然不可避免的对社会和生产造成了破坏,但更多的是促进了各民族之间血统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另外,不少民族割据政权,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实力,都会学习汉族较高的生产技术和主动任用汉族硕学名士。
张骞的凿空西域与丝绸之路的开通,是横跨欧亚大陆、长达7000多公里的东西方贸易之路的开通。此路通于西汉武帝时期,盛于隋唐,衰落于宋元。古丝绸之路自中原出发,远至地中海地区,形成了南北中三道,甘肃则是每一条道路的必经之地。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地区的丝绸传入西域、印度、中亚、西亚乃至欧洲、非洲,西域的汗血马、苜蓿、胡桃(核桃)、胡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石榴等物产和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以及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也随之传入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域的各个民族,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和非洲的不少国家,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即使在海上交通开辟之后,这条陆上通道也并未废弃。可以说汉唐时期的甘肃,在中西交通史和民族、文化及宗教的传播和融合上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