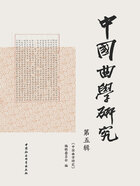
词曲音乐研究
论法曲在词乐中的演进[1]
张春义
内容摘要:学界虽对法曲界定存有争议,但对法曲作为燕乐重要组成部分及对词乐贡献之认识,却颇为一致。今以法曲在词乐中的演进为考察中心,略述法曲对词乐的贡献。又通过曲破、转踏、诸宫调、杂剧及院本等保留的法曲成分,考察法曲虽“解体”于宋、金,然亦于宋、金时期重获新生,并证“法曲亡于宋”之说不可信。
关键词:法曲 清乐 隋唐燕乐 词乐演进 宋金曲乐
一 “法曲”与“隋唐燕乐”的关系
法曲之名,较早见于《新唐书·礼乐志十二》[2]。学界有关法曲的界定、由来及与隋唐燕乐的关系仍有很大分歧,但有两点在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
(一)法曲与清乐的关系
法曲起于隋而盛于唐,其音乐特征是“清而近雅”。《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3]其声始出清商部,在音乐特征方面比较接近清乐。这集中表现在律和器两方面:
第一,关于法曲的律。《乐书》卷一八八:“法曲兴自于唐,其声始出清商部,比正律差四,郑、卫之间。”[4]明言法曲出于清商部,而比正律差四律,此乃就唐法曲而言。《梦溪笔谈》:“今乐部中有‘三调乐’,品皆短小,其声噍杀,唯道调、小石法曲用之。虽谓之‘三调乐’,皆不复辨清、平、侧声,但比他乐特为烦数耳。”[5]所谓“三调乐”,指的是清乐“清、平、瑟三调”,而“唯道调、小石法曲用之”云云,则说明北宋法曲部与清乐仍有关系。据考,“法曲既本自清商,当亦为清商短律”“法曲仅为清乐之分支,且其律犹为清商短律小调式”。其律乃源于荀勖笛律(黄钟管以四倍正律之姑洗为度,其律仍为A调),故法曲之律当以A为黄钟,其律比宋代俗乐教坊律之黄钟(D)差四律[6]。证明唐宋法曲皆出清商部,而自唐至宋其律亦未尝有变。
第二,隋法曲“音清而近雅”,音乐特点较近清乐。按隋法曲乐器有铙、钹、钟、磬、幢箫、琵琶6种(《新唐书·礼乐志十二》,《乐书》卷一八八),而清商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15种(《乐府诗集》卷九六)。隋法曲乐器虽比清商乐少,但钟、磬、幢箫、琵琶等几种主要乐器源于清乐,铙、钹等几种乐器可能源于胡乐(《乐书》卷一二五,《通考·乐考七》)。从乐器这一项说隋代法曲源于清乐[7],是行得通的。
因法曲、清乐特殊的亲缘关系,又易为“非此即彼”的逻辑思维左右。如:“隋唐俗乐是以‘法曲’为主线,沿清商乐发展而来的,并不是胡乐或印度的影响为主。”[8]疑非定论。据丘先生考证,发现法曲是“以清商为基本再融合部分的道曲佛曲以及若干外族乐而成的一种新乐”[9]。当更可信。
(二)法曲与“新燕乐”的关系
法曲最初近似于清乐,后渐与胡乐结合,成为新燕乐的组成部分。但法曲与清乐比,仍有较大不同:
第一,法曲宫、商、角、徵、羽五调,不同于清乐三调[10]。《旧唐书·音乐志三》:“(开元二十五年)时太常旧相传有宫、商、角、徵、羽《燕乐》五调歌词各一卷,或云贞观中侍中杨恭仁妾赵方等所铨集。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至(韦)縚又令太乐令孙玄成更加整比为七卷。又自开元已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孙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传谓为法曲。”[11]关于“相传谓为法曲”的“《燕乐》五调歌词”,学界或云非属燕乐范畴[12]。按,所谓“法曲五调”,与“燕乐二十八调”并不矛盾。《宋史·乐志四》:“(政和三年五月)诏曰:‘……以《大晟乐》播之教坊……’于是令尚书省立法,新徵、角二调曲谱已经按试者,并令大晟府刊行,后续有谱,依此。其宫、商、羽调曲谱自从旧。”[13]知唐宋燕乐曲谱实亦按“宫商角徵羽五调”编排,可证“相传谓为法曲”的“《燕乐》五调歌词”,亦属燕乐范畴。
第二,法曲虽源于清乐,但自隋代始即有胡乐成分。《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隋炀帝厌其声澹,曲终复加解音。”所谓“解音”,当即“解曲”。《羯鼓录》:“凡曲有意尽而声不尽者,须以他曲解之。”《乐书》卷一六四:“凡乐以声徐者为本声,疾者为解。自古奏乐,曲终更无他变。隋炀帝以清曲雅淡,每曲终多有解曲。”其用乐手法大异于清商乐,也不同于隋初法曲,其实更接近隋唐燕乐[14]。据研究,《隋书·音乐志》所载九部伎有“解曲”的伎乐中,均为“歌曲—解曲—舞曲”的“多遍连章”结构,即“隋时法曲样式”[15]。它与隋初法曲“音清而近雅”“曲终更无他变”的奏乐之法有很大不同,实为新燕乐用乐手法。
关于法曲结构,学界多举白居易《霓裳羽衣歌》为例,即散序、中序、入破、尾声。其中“入破”,颇类似于隋代的解曲。据研究,“解音”具有“急遍”性质。隋炀帝时法曲“曲终复加解音”,演变为唐太宗朝有“入破”的法曲样式(《乐书》卷一六四),已很难说就是纯粹的“华夏正声”,实为一种胡乐成分很重的新燕乐。如《霓裳羽衣歌》主体部分为胡乐《婆罗门》,且《婆罗门》用于中序的可能性最大[16]。史载酷爱法曲的唐玄宗(《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其所“爱”即为此类掺入胡乐的法曲。
法曲虽与胡乐合流,成为“新燕乐”(隋唐燕乐)的一部分,但仍然在器、律及音乐表现方面保持独立特性。
其一,法曲之器与胡部燕乐仍有不同。上引《笔谈》“品皆短小,其声噍杀,唯道调、小石法曲用之”云云,“品”疑为“器”之误,乃指法曲部乐器短小;又《词源》所谓法曲“以倍四头管品之”,燕乐大曲“以倍六头管品之”[17],即指法曲与胡部燕乐所用乐器之异。
其二,法曲之律也与胡部燕乐各自划域封疆。据刘崇德先生考证,唐清乐、法曲仍保留其律,至天宝十三载(754)法曲与胡部合奏,“胡部律与清乐律重合”“所谓燕乐音阶得以确立”“而清乐乐调至宋代尚有孑遗,如法曲尚与燕乐大曲争一席之地”[18]。
其三,乐曲结构方面,唐宋“大曲、法曲两分明”。有催、衮者为燕乐大曲,无催、衮而有散序、歌头者为法曲。《宋史·乐志六》:“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无是也。”[19]音乐表现方面,法曲清越,音声近古;大曲流美,与胡乐相近。《词源》:“若曰法曲,则以倍四头管品之,其声清越。大曲则以倍六头管品之,其声流美。”“法曲有散序歌头,音声近古,大曲有所不及。”[20]法曲音律节奏与燕乐大曲相异。
二 法曲在词乐中的演进
“词乐”常被视为“宋乐”,不过指成熟形态的词乐而论,其形成实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形态。如果说词乐传统是一条河的话,那么,法曲应该是其中一条重要支流。
(一)法曲在词乐形成期的作用
法曲在词乐中的演进,首先要从法曲在词乐形成期的作用说起。如果视词乐为宋乐,则宋法曲仅有《道调宫·望瀛》和《小石调·献仙音》仍为教坊演奏(《宋史·乐志十七》,《乐书》卷一八八),它与宋代词乐关系显然不能和“胡部燕乐”相比。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如上所述,法曲在燕乐形成和发展中有极重要作用,尽管词乐并不等于燕乐,然考察法曲在词乐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也当作如是观。
众所周知,词乐形成与唐教坊关系密切,而教坊主要功能就在演奏以清商部“九代遗声”与法曲为主的燕乐曲。史载,开元二年(714)唐玄宗重立教坊以演奏燕乐新曲,其中梨园法部是专门演奏法曲的新设机构。著名词调《荔枝香》即产生于梨园法部中的“小部音声”[21]。史料充分说明,燕乐曲子形成与开元二年的重置教坊有关。
据考察,因胡部器乐、舞乐性质与传统华夏声乐歌唱系统有异,胡部燕乐杂曲和舞乐曲经历了漫长演变过程方形成声乐系统的曲子,故词体并非直接产生于胡部器乐和舞乐[22]。近来研究也表明:“曲子主要是以中原本土六朝清乐为主体,以胡乐为参用,以声乐演唱为主要形式的音乐。盛唐时期,经历法曲的中间环节,声乐曲子开始发生。”[23]尽管将法曲作为曲子发生直接激发剂的说法尚需作补证,但在重视唐法曲对词乐形成作用方面,应是有积极意义的。
燕乐曲子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其中法曲起了多大作用,以及曲子是用何种形式的节拍演唱,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认为,就法曲而言,也有隋法曲与唐法曲之分,它们在词乐形成阶段所起作用是很不相同的。初唐法曲“《燕乐》五调歌词”(一说“隋法曲”)到了盛唐“工人多不能通”,原因在于“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这与天宝十三载(754)诏令“道调、法曲与胡部合奏”及“合胡部者为宴乐”的记载相合,说明盛唐法曲歌法与初唐法曲(或隋法曲)有很大不同。盛唐歌者所唱已非初唐法曲,而是“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所包含的成分更复杂。尽管法曲在盛唐燕乐中仍占重要地位,但恐怕不能视为“声乐曲子开始发生”的唯一因素。史载“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而“多不能通”“《燕乐》五调歌词”的法曲[24],说明“胡夷里巷之曲”还是占有重要地位。“胡夷之曲”指的就是胡部燕乐。再者,燕乐曲子演唱的节拍,一般来说应该是用“句拍”,其乐器依托于拍板,恐怕像隋法曲那种缺少拍板的乐器“部当”难以承担。原生形态的隋或初唐法曲“《燕乐》五调歌词”,为什么到了盛唐“工人多不能通”,这可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二)唐代词乐中的法曲词调
法曲在词乐中的演进,更为明显的是法曲与词调音乐的关系。词调音乐有不少可溯源于法曲,如《碧鸡漫志》《词源》都将词的起源远溯于隋[25]。据考,隋曲有《泛龙舟》《穆护子》《安公子》《斗百草》《水调》《杨柳枝》《河传》7调为词乐之源[26]。其中《泛龙舟》《斗百草》2曲可大致定为法曲。隋曲有词流传者有《纪辽东》和《上寿歌辞》,正史列为“雅乐歌辞”,未列入白明达所造“新声”范围(《隋书·音乐志下》)。然从其名称看,也与清商乐有相近之处,亦可能是清商乐与胡乐糅合形态的新曲。
关于隋代法曲曲目和数量,目前还没有统一说法。史载隋乐正白明达造新声14曲(《隋书·音乐志下》),其中《万岁乐》《斗百草》《泛龙舟》3曲,唐演变为法曲,则其在隋本身即为法曲的可能性很大,很可能就是“曲终复加解音”的隋法曲之变种[27]。另外,有可能属于隋法曲的前世曲子,如《王昭君》《思归乐》《五更转》《玉树后庭花》《饮酒乐》《堂堂》6个曲目,在唐代尚有燕乐歌词可考,其中《王昭君》《五更转》《玉树后庭花》,即使在宋代词乐中尚可找到遗踪所在。
法曲风行于盛唐,并设有专教习法曲的梨园和太常梨园别教院。《唐会要》:“太常梨园别教院,教法曲乐章等:《王昭君乐》一章,《思归乐》一章,《倾杯乐》一章,《破阵乐》一章,《圣明乐》一章,《五更转乐》一章,《玉树后庭花乐》一章,《泛龙舟乐》一章,《万岁长生乐》一章,《饮酒乐》一章,《斗百草乐》一章,《云韶乐》一章,十二章。”[28]唐法曲曲目和数量极多。《乐书》卷一八八:“法曲兴自于唐……太宗《破阵乐》、高宗《一戎大定乐》、武后《长生乐》、明皇《赤白桃李花》,皆法曲尤妙者。其余如《霓裳羽衣》《望瀛》《献仙音》《听龙吟》《碧天雁》《献天花》之类,不可胜纪。”“不可胜纪”云云,说明其曲目和数量已难以统计。丘琼荪先生认为唐法曲可考者有“二十五曲”[29];刘崇德先生对“二十五曲”细加考订,辨《云韶乐》《荔枝香》《雨铃霖》非法曲,共得22曲,如:
《王昭君》《思归乐》《倾杯乐》《破阵乐》《圣明乐》《五更转》《玉树后庭花》《泛龙舟》《万岁长生乐》《饮酒(乐)》《斗百草》《大定乐》《赤白桃李花》《霓裳羽衣》《望瀛》《献仙音》《听龙吟》《碧天雁》《献天花》《火凤》《堂堂》《春莺啭》。[30]
通观初唐、盛唐及中、晚唐法曲演进状况,其中不乏词乐成分。据考,唐五代词调有76调来源于教坊曲。可溯源于法曲的词调,有《倾杯乐》《破阵乐》《破阵子》《小秦王》《拂霓裳》《法曲献仙音》《昭君怨》《后庭花》《雨淋铃》《荔枝香》等。如:
(1)《王昭君乐》。《唐会要》:“教法曲乐章等:《王昭君乐》一章。”[31]《唐声诗》收《王昭君》“五言八句四平韵”一首,并云:“本汉曲,晋以后为舞曲及琴曲。入唐为吴声歌曲,玄宗开元间入法曲。”“唐僧唱佛曲之前,亦有转《明妃》多遍者。”“《大日本史》三四八性调内列《王昭君》:‘汉乐也。古乐,中曲,十拍,无舞。’《东洋历史大辞典》载日本《王昭君》有雅曲《尺八谱》。”[32]词乐中有《昭君怨》。
(2)《倾杯乐》。一名《古倾杯》《倾杯》。《唐会要》:“教法曲乐章等……《倾杯乐》一章。”[33]《教坊记》“曲名”条有《倾杯乐》,则《倾杯乐》亦为教坊曲。敦煌曲谱收有《倾杯乐》急、慢二谱,另有长安白道屿教衍和尚抄本《倾杯乐》曲谱[34],均属器乐谱。据考,《倾杯乐》源于晋“杯盘舞”,属清乐;北周为登歌,唐初用龟兹乐,则已“胡化”;盛唐为“法曲”[35]。《理道要诀》载《倾杯乐》为中吕商(时号双调),《羯鼓录》载为“太簇商”。《乐府杂录》载《新倾杯乐》。宋柳永《乐章集》有《倾杯乐》八首,属大石调、林钟调、羽调、散水调。
(3)《破阵乐》。《唐会要》:“教法曲乐章等……《破阵乐》一章。”《教坊记笺订》:“《破阵乐》,太宗创始,乐用清商,乃‘法曲之尤妙者’。”[36]《唐声诗》收《破阵乐》“五言四句二平韵”“六言八句五平韵”与“七言四句三平韵”各一首[37]。唐《破阵乐》属大食调、小食调、越调、双调、水调。宋有《正宫·平戎破阵乐》大曲及《破阵乐》慢曲。
(4)《斗百草》。隋曲,出自龟兹人白明达所创新声(《隋书·音乐志下》);盛唐演变为法曲。《唐会要》:“教法曲乐章等……《斗百草乐》一章。”[38]《斗百草》风行于盛唐及中唐。敦煌词有《斗百草》四首,任二北考证为盛唐词。宋词有《斗百草》《斗百花》二调[39]。
(5)《霓裳羽衣曲》。《教坊记笺订》:“《霓裳》,应为《霓裳羽衣曲》之简称……白居易新乐府曰:‘法曲法曲舞《霓裳》’,为法曲无疑。”[40]宋人考证甚详。《碧鸡漫志》:“《唐史》云:‘河西节度使杨敬述献’,凡十二遍……杜佑《理道要诀》云:‘天宝十三载七月,改诸乐名。中使辅璆琳宣进止,令于太常寺刊石,内《黄钟商·婆罗门曲》改为《霓裳羽衣曲》。’”[41]《教坊记笺订》定为道调、清乐。据考,其“歌与破则是在吸收凉州所进天竺的《婆罗门》曲调续写而成的”(详上)。宋词调有《霓裳中序第一》等。
(6)《荔枝香》。周紫芝《荔枝香》:“梨园法曲凄且清,相传犹是隋家声。”“隋家声”云云,考宋人多将“词的起源”远溯于隋,实《荔枝香》本为唐代梨园法曲。《新唐书》“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42]云云可证。“小部”即梨园法部之“小部音声”,可见《荔枝香》也属盛唐法曲之一。宋柳永、周邦彦皆有《荔枝香》词,属歇指调。《碧鸡漫志》:“今歇指调、大石调皆有近拍,不知何者为本曲。”[43]
通过以上6调的考察,可知法曲与清乐的关系及法曲在“胡乐汉化”中的作用。其中《倾杯乐》一曲尤为典型。《倾杯乐》其始为清商乐,或谓起于晋人之杯盘舞;北周有《倾杯曲》,则为胡乐(《隋书·音乐志下》)。至唐初为大曲,用龟兹乐,长孙无忌等人作辞[44]。至盛唐,乃为法曲。据此,知法曲《倾杯乐》实为清乐与胡乐糅合形态的新曲。从敦煌曲谱《倾杯乐》之急、慢二体,到宋词乐《倾杯乐》八体,实又经历了从舞曲、器乐曲到曲子的变化。其逐渐演变成词乐的过程,本身即是考察法曲渊源及其在隋唐燕乐与唐宋词乐中地位的“活标本”。
(三)宋代词曲音乐中的法曲踪迹
后世词曲音乐中,仍有法曲踪迹。《宋史·乐志十七》:“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调宫《望瀛》,二曰小石调《献仙音》。乐用琵琶、箜篌、五弦、筝、笙、觱栗、方响、拍板。”[45]按:宋法曲《道调宫·望瀛》《小石调·献仙音》实均传自于唐,然云二曲来自唐《霓裳羽衣》法曲,则误;宋人或指《望瀛》即《霓裳羽衣曲》,亦误[46]。
其实,宋法曲确实不止此二曲。蔡襄《杂说》:“(钧容乐工任)守程精通音律,悼其亡缺,仿像法曲造之,寄林钟商。华(花)日新亦造《望瀛》《怀仙》二曲,世人罕得其本也。”[47]《嘉祐杂志》:“同州乐工翻河中黄幡绰《霓裳谱》,钧容乐工程士守以为非是,别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见之,题其后云:‘法曲虽精,莫近《望瀛》。’”[48]就有法曲《怀仙》,或为教坊伶人花日新所造。又,《武林旧事》:“第十二盏,诸部合《万寿兴隆乐》法曲。”[49]则又有《万寿兴隆乐》法曲,大概为南宋人新制法曲。以上均为北宋教坊或南宋教乐所演奏法曲的情况,乃属于宫廷音乐范畴。
宋代民间也有演奏法曲情况,大多在州郡及私家宴会。郑獬《次韵程丞相重九日示席客》:“《霓裳》法曲古来绝,小槽琵琶天下尤。”小注:“公之佳妓善《霓裳》法曲,而胡琴尤绝。”[50]所谓“《霓裳》法曲”,即唐代法曲《霓裳羽衣曲》,乃为私家宴会佳妓演奏。又,沈遘《使还,雄州曹使君夜会,戏赠三首》其二:“法曲新声出禁坊,边城一听醉千觞。明朝便是南归客,已觉身飞日月傍。”[51]考曹诵元祐六年(1091)四月至绍圣元年(1094)知雄州[52],此时边城雄州宴会,也可听到教坊法曲演唱。此风至南宋未衰。陆游《忆唐安》:“红索琵琶金缕花,百六十弦弹法曲。曲终却看舞《霓裳》,袅袅宫腰细如束。”(《剑南诗稿》卷一一)亦为州郡宴会佳妓演奏法曲情况。《浩然斋雅谈》卷中:“放翁《咏长安富庶》有云:‘红桑琵琶金镂花,百六十弦弹法曲。’盖四十面琵琶也。”所用有“四十面琵琶”,可见民间演奏法曲之盛况。不仅如此,宋演奏法曲情况遍布于大江南北,并未受到空间地域的限制。韩琦《醉白堂》:“其间合奏散序者,童妓百指皆婵娟。”[53]又,韩琦《(寄致政赵少师)又寄二阕》其一:“芳樽屡酌瀛洲上,谁听《霓裳》散序声。”[54]“散序”“《霓裳》散序”云云,皆指法曲而言,此为河北相州演奏法曲盛况。陈襄《荔枝歌》:“番禺地僻岚烟锁……凤箫呜咽流宫商。醉歌一曲《荔枝香》,席上少年皆断肠。”[55]《荔枝香》为唐法曲,两宋市井歌妓不乏以演唱此曲知名者,此为广东番禺演奏法曲的情况。与此同时,宋演奏法曲盛况也激发了民间收集整理法曲的风气。据袁桷《外祖母张氏墓记》:“惟太傅(史弥坚)婿赵崇王,悉祖《乐髓景祐谱》,调八十四,穿心相通……丁抗掣曳,大住小住,为喉舌纲领。法曲散序,忠宣(史弥坚)删正之。”[56]知淳熙十年(1183)后四明史浩家校谱、订谱之事,也与“法曲散序”有关。
关于法曲在宋代的存留问题,曾经有所谓“法曲亡于宋”的说法。主要是据《宋史·乐志》所录宋法曲仅为二调而立论,乃仅从数量观察而未从演变角度探讨。如上所述,宋代法曲演奏教坊—州郡衙前乐营—私家宴会—市井勾栏的演变过程,与其说是“法曲亡于宋”的表征,不如说是法曲在宋代获得新发展的证据。
按隋唐法曲多用于抒情歌舞,用于叙事当始于宋。文献所录曾慥增损石延年《般涉调·拂霓裳》曲及王平所得《夷则商·霓裳羽衣》谱,即为叙事之曲。今考“普府守山东人王平”“自言得《夷则商·霓裳羽衣》谱”云云[57],当为州郡乐人所作,而为普州守王平所得。其性质虽属官府,但渊源当出于民间。又,考唐法曲《霓裳羽衣曲》包括散序、中序、入破、尾声,与宋人《夷则商·霓裳羽衣》谱不同,据《宋史·乐志六》:“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无是也。”[58]王灼所谓“音律节奏,与白氏《歌》注大异。则知唐曲,今世决不复见,亦可恨也”[59],知唐法曲《霓裳羽衣曲》失传已久。宋人王平所得《夷则商·霓裳羽衣》谱,显系州郡乐人伪托唐谱,而伪造时间当在政和四年(1114)至宣和元年(1119)[60]。
又,《碧鸡漫志》所录曾慥增损石延年旧辞《般涉调·拂霓裳》曲[61],可能亦用于州郡宴会。据考,“《夷则商·霓裳羽衣》谱”“《般涉调·拂霓裳》曲”云云,二者皆托名“《霓裳》法曲”“开、宝遗音”,实乃宋人自造,其性质已属大曲和转踏,乃非法曲原声。所谓“大曲、法曲两分明”[62],唐时已如此,宋更不乏例。其实,和大曲命运一样,法曲在宋代也逐渐“解体”衍变。一些源自唐大曲的新曲艺形式(如曲破、转踏、缠达、缠令、诸宫调、唱赚等),均不断吸收法曲营养,并将它纳入新的发展体裁之中。上引曲破“《夷则商·霓裳羽衣》谱”、转踏“《般涉调·拂霓裳》曲”云云,二者虽伪托“《霓裳》法曲”“开、宝遗音”,尽管在崇尚“法曲原生态”的考证者眼里,确实是“唐曲今世决不复见”的证据,但从流传与衍生角度看,又未尝不是法曲在宋获得新发展的证据。
今考宋法曲的“解体”,其实也是法曲在宋代衍变并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法曲不仅在宋民间演奏,而且在词曲音乐中也留下了踪迹。如,词调音乐中《破阵乐》《破阵子》《霓裳中序第一》《法曲献仙音》《法曲第一》《昭君怨》《后庭花》《雨淋铃》《荔枝香》等,皆唐法曲入词乐之可考者。又,法曲还被用于杂剧、院本之中。今传南宋“官本杂剧段数”、金“院本名目”等,均有法曲身影[63]。所谓“官本”“院本”者,其始皆当系教坊为宫廷演出的本子,后流入市井勾栏,成为民间演出之本。《东京梦华录》:“教坊、钧容直每遇旬休按乐,亦许人观看。每遇内宴前一月,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作乐杂剧节次。”又:“教坊减罢并温习: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称心等,般杂剧。”[64]知教坊为宫廷演出的本子流入市井勾栏,在崇宁、大观(1102—1110)以来京瓦伎艺中就较为常见。王国维先生说:“曰‘和曲院本’者,十有四本。其所著曲名,皆大曲、法曲,则‘和曲’殆大曲、法曲之总名也。”[65]吕洪静先生认为:“这可看作是13世纪法曲音乐体段用于搬演‘杂剧段数’的一个信息。”[66]所言甚是。
综上所述,法曲在宋代的演变和衍生,一方面促使了它在民间的传播,另一方面又使它依托于其他曲艺载体获得“重生”的机遇。其中法曲由抒情到叙事的转型,学界不少人把它作为后世词曲音乐得以兴盛的一个契机。证以宋代曲破、转踏、诸宫调、杂剧及金院本等保留的法曲成分看,可知宋、金时期法曲仍在流行。所谓“法曲亡于宋”之说,并不可信。随着音乐考古学中“曲调考证”的进一步深入,法曲在宋代词曲音乐中的踪迹,将会越来越被人们揭示并得到认可。
[作者简介]张春义,嘉兴学院文法学院中文系教授。有专著《大晟府及其乐词通考》。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宋词声律史研究”(13BZW070)阶段成果。
[2]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6页。
[3]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十二》,第476页。
[4] 陈旸:《乐书》卷一八八《法曲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沈括撰,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五《乐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193页。
[6] 刘崇德:《燕乐新说》,黄山书社2003年版,第25—26页。
[7] 丘琼荪撰、隗芾辑补:《燕乐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1页。
[8] 黄翔鹏:《中国古代音乐歌舞伎乐时期的有关新材料、新问题》,《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
[9] 丘琼荪撰、隗芾辑补:《燕乐探微》,第99页。
[10] 按:清乐有平调、清调、瑟调三调,又有楚调、侧调(《隋书·音乐志下》,《通典·乐六》,《乐府诗集》卷二六)。
[1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三○《音乐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89页。
[12] 详见李石根《法曲辩》(《交响》2002年第2期)、丘琼荪《燕乐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13] 脱脱等:《宋史》卷一二九《乐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18—3019页。
[14] 详见刘尊明《隋唐宫廷音乐文化初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2期。
[15] 吕洪静:《唐时大曲、法曲两分明》,《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16] 详见高人雄《从〈教坊记〉曲目考察词调中的西域音乐因子》(《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王安潮《唐大曲考》(博士学位论文,上海音乐学院,2007年油印本,第85页)。
[17] 张炎:《词源》卷下,《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5页。
[18] 刘崇德:《燕乐新说》,黄山书社2003年版,第27、48页。
[19] 脱脱等:《宋史·乐志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53页。
[20] 张炎:《词源》卷下,《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5页。
[21] 欧阳修等:《新唐书·礼乐志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6页。
[22] 详见刘崇德《燕乐新说》(黄山书社2003年版,第221页)、李昌集《华乐、胡乐与词:词体发生再论》(《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
[23] 王洪、孙艳红:《略论曲词不产生于燕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4] 刘昫等:《旧唐书·音乐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89页。
[25] 详见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4页)、张炎《词源》卷下(《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5页)。
[26] 详见《碧鸡漫志》卷五(第104—117页);唐圭璋、潘君昭《论词的起源》(《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27] 王运熙:《清乐考略》,《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220页。
[28] 王溥:《唐会要》卷三三《雅乐下》,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14页。
[29] 丘琼荪撰,隗芾辑补:《燕乐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30] 刘崇德:《燕乐新说》,黄山书社2003年版,第28页。另参周期政《唐代乐舞歌辞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04年油印本,第71—89页)。左汉林认为唐代法曲可考者有“二十四曲”(《唐代梨园法曲性质考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31] 王溥:《唐会要》卷三三,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14页。
[32] 任二北:《唐声诗》下册,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146、150页。
[33] 王溥:《唐会要》卷三三,第614页。
[34] 李健正:《大唐音乐风情》,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35] 详见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95、227页)、高人雄《从〈教坊记〉曲目考察词调中的西域音乐因子》(《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张开《唐〈倾杯乐〉考论》(《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6期)。
[36] 任二北:《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2页。
[37] 任二北:《唐声诗》下册,第21页。
[38] 王溥:《唐会要》卷三三,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14页。
[39] 详见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216页)、田玉琪《词调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40] 任二北:《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3页。
[41] 王灼:《碧鸡漫志》卷三,《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5页。
[42] 欧阳修等:《新唐书·礼乐志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6页。
[43] 王灼:《碧鸡漫志》卷四,第109页。
[44]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四六《乐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22页。
[45] 脱脱等:《宋史·乐志十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49页。又见《乐书》卷一八八、《文献通考·乐考十九》。
[46] 详见《宋史·乐志六》(第3053页)、《词源》卷下(《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6页)、《六一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1页)、《梦溪笔谈校证》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4页)、《碧鸡漫志》卷三(《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7页)、《韵语阳秋》卷一五(《历代诗话》本)。
[47] 蔡襄:《蔡襄集》卷三四《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21—622页。
[48] 王灼:《碧鸡漫志》卷三,第97页。
[49] 周密撰、周峰点校:《武林旧事》卷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
[50] 郑獬:《郧溪集》卷二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 沈遘:《西溪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 李之亮:《宋河北河东大郡守臣易替考》,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14—115页。
[53] 韩琦:《安阳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 韩琦:《安阳集》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5] 陈襄:《古灵集》卷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 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卷三三,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47页。
[57] 王灼:《碧鸡漫志》卷三,《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8页。
[58] 脱脱等:《宋史·乐志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53页。
[59] 王灼:《碧鸡漫志》卷三,第98页。
[60] 详见张春义《大晟府及其乐词通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页。
[61] 王灼:《碧鸡漫志》卷三,第98页。
[62] 详见吕洪静《唐时大曲、法曲两分明》(《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李石根《法曲辩》(《交响》2002年第2期)。
[63] 《武林旧事》卷一○《官本杂剧段数》:“《狐和法曲》《藏瓶儿法曲》《车儿法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页);陶宗仪撰、文灏点校《辍耕录》卷二五《院本名目》:“和曲院本:《月明法曲》《郓王法曲》《烧香法曲》《送香法曲》。”“诸杂院爨:《闹夹棒法曲》《望瀛法曲》《分拐法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
[64] 孟元老撰,周峰点校:《东京梦华录》卷五,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65]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66] 吕洪静:《宋时“法曲”音乐结构样式辨识及对人文关照的质疑》,《交响》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