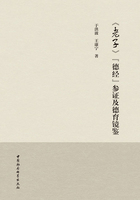
第1章 《总论》:《老子》的“破”与“立”
作为本书的“总论”,下文分四章对理解《老子》关键所在的三个核心问题予以阐述与分析。第一章为《〈老子〉的“破”与“立”》;第二章为《〈老子〉的“道”与“德”》;第三章为《〈老子〉的“无为”与“自然”》;第四章是《本书的撰写体例》。
在第一章中,主要以老子所处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为切入点,以西方学者提出的“哲学的突破”,结合庄子所谓的“道术将为天下裂”为分析框架,以老子和孔子针对“礼崩乐坏”的大变局提出的“救时之弊”的主张为参照,比较老子和孔子“哲学的突破”的“创新”所在。第二章对“道”与“德”的“形上本体”与“形下器用”之间的特征、功能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与比较。《老子》“五千言”,不出“道”和“德”二字,但是“道”和“德”的特性及其主旨所归,却在于“无为”和“自然”。故而,本书“总论”部分专设第三章,以对二者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予以分析。“无为”和“自然”,作为《老子》“形上之道”的根本特征,一旦落实到人间万物,其功用价值可谓巨细无遗。第三章主要对“治者”的“无为”与“百姓”的“自然”以及二者的关系予以阐述与分析。本书“总论”的三章所涉及的三个核心问题,可谓解读《老子》“五千言”的肯綮所在,“总论”中对这三个问题的理解与解释,亦贯穿于本书正文对《老子》“德经”各章的解读之中。本书作者认为,《老子》“五千言”的世界观,大致可归结为“以道观天地”“以道观人”和“以道观万物”的“常道观”,唯有以老子“常道观”的高度解读和体悟《老子》,方能得其真谛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产生及其学术繁荣,并非突兀的空穴来风。庄子在描述当时的社会局势与学术裂变的关系时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从庄子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三个基本推断。其一,当时的诸子百家产生于“天下大乱”的时代格局;其二,正是由“天下大乱”而导致的“道术”裂变,方有诸子百家各执一端进而成就各自的学说;其三,由于诸子百家各执一端,故而其学统业已失却裂变之前的“道术”一统。
庄子所谓的“道术将为天下裂”,与美国学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所谓“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者,庄子强调的是在“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后,由于诸子各执一端,故而其学说“不幸”失却了固有“道术”之“大体”;而帕森斯所谓的“哲学的突破”,则重在强调“突破”之后世界各大古代文明学术上的高度繁荣。若以“道术将为天下裂”和“哲学的突破”作为分析框架,对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和儒家的学统渊源予以比较分析,或可对《老子》的主旨及其特征有更为深入的诠释。
美国学者帕森斯所谓的“哲学的突破”,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提出的“轴心时代”(axial times)这一概念有诸多相似之处。至于二者概念的缘起及相互借鉴等问题,此不赘述。综合“哲学的突破”与“轴心时代”两个概念,大凡有以下诸内涵。其一,大约在公元前第一个一千年的“轴心时代”里,在希腊、印度、以色列和中国这“四大文明古国”或曰“四大文明摇篮”中,不约而同地经历了一次“哲学的突破”;其二,这次“突破”性的认识成果在文化、教育和学术等领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繁荣,并为此后各大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影响深远的传统“原型”;其三,在“哲学的突破”的过程中,第一批专心于学术的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如古希腊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的众多哲学家、古以色列的先知、中国的孔、孟、老、庄等;其四,由于各大古代文明古国所处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因而其“哲学的突破”的主题、模式和结果等亦迥然有别。
可以说,任何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学说,大致都具备三个基本特征。其一,能够突破并超越当时的学术范式及其学术体系的局限,进而建构起更具普适性的理论体系;其二,能够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之流弊有透彻的认识,并能开出“救时之弊”的方略;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对“道与器”“天与人”“体与用”等终极性的问题,具有超越性的洞识且兼具经世致用的关切。下文拟以“道术将为天下裂”和“哲学的突破”的概念为分析框架,以儒家和道家相互比较的视角,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儒道两家拟“突破”的主题及其所“创立”学统的主旨等相关问题予以回顾、分析与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所要“突破”的对象,乃是濒于“崩坏”的礼乐文化。礼乐文化产生于夏,发展于商,成熟于周。据史载,周公鉴于夏商两代的礼乐制度及其得失,对其增减损益,重新制礼作乐而得以完善。正如孔子所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究其渊源,礼乐文化是由上古社会的“巫”文化和敬天礼地的原始宗教演变而来。正如《礼记·乐记》所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又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载:“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制礼作乐者认为,“礼乐”乃世间万物赖以生存的天地之道,生存于天地之间的人类社会亦当尊而行之。西周在“制礼作乐”完善“礼乐文化”的同时,又根据血缘亲疏、事功大小、大宗小宗等进行封土建国,从而形成了封建制度。通常而言,西周的礼乐文化亦包括封建制度;抑或说,封建制度与礼乐文化始终相生相伴,表里为一。究其实,礼乐文化既是一套带有些许上古社会沟通“天人关系”的神学遗风惯俗,又是一套与封建制度相生相伴的文化体系;既是一套区分亲疏贵贱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又是一套规训臣民安分守己的“礼乐教化”体系。可以说,礼乐文化和封建制度的有机结合,实可谓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又是道统、政统和学统的统一。
但是在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权威性开始衰微,封建制度和礼乐文化亦渐趋式微,整个社会陷于诸侯争霸、战火不断、“礼崩乐坏”的大变局之中。此时,沿袭自夏商周三代的“学在官府”和“官师合一”的文化和教育垄断局面,逐渐被“文化下移”和“私学兴起”所取代。此时,大多由原来“王官”蜕变而成的“诸子百家”,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迫切需要证明各自“道统”和“学统”的正统性和权威性。由是,诸子们纷纷托古论道,针砭时弊,激荡学问,一时形成蔚为大观的学术繁荣。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曾频频论道,诸如,“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他甚至感慨“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但是孔子之论道,并非为论道而论道,大多是出于对当时“失道”现象的感慨,其论道的最终目的乃是“克己复礼”;抑或说,要恢复到西周早期由周公所创设的礼乐文化和封建制度。孔子痛惜于当时“礼崩乐坏”的大变局,试图通过游说诸侯实施“仁政”而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在孔子看来,西周时期实施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层层分封制度,符合理想的血缘—宗法大家族中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嫡庶有别的等级序列。”[1]在他看来,导致“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既在于人们不能克制自己不合理的欲求,即如其所谓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又在于人们只重视礼乐的外在仪式,而失却了礼乐的内在诚意,即如其所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更在于当时的礼乐文化缺乏“仁”的精神内核,如其所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为此,孔子开出了“克己复礼为仁”的道德“四目”,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以挽救“礼崩乐坏”的残局。孔子认为,以自律的道德“四目”为基础,加之“学”“习”“问”“省”等自我修为,即可达到“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自觉境界。
总之,孔子试图赋予濒于“崩坏”的“礼乐文化”以内在的“仁”为精神内核,其用意既在于反对诸侯枭雄们以“周礼”之名行“霸权”之实的吞并战争,又在于与其他诸子百家学术的据理抗争。正如著名学者李泽厚所言:“孔子用‘仁’解‘礼’,本来是为了‘复礼’,然而其结果却使手段高于目的,被孔子所挖掘所强调的‘仁’——人性的心理原则,反而成了更本质的东西,外在的血缘(‘礼’)服从于内心的(‘仁’)。”[2]就“哲学的突破”来看,孔子所创立的“仁学”当属于温和的改良主义,其学说的目的是“克己复礼为仁”而非颠覆“周礼”;其“托古创新”之处在于,将人之为人之本性的“爱人之仁”,升华为“礼乐教化”的灵魂;其首要的“突破”在于,业已超越了外在的、他律的“礼”,而转向反求诸己的、内在的、自律的“仁”。此后,以“仁学”为基础,儒家逐渐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道德谱系的人道主义的哲学体系。
相较于孔子所创设的“仁学”的温和改良主义特点,老子学说“哲学的突破”则具有明显的激进主义意味。此处所谓的“激进主义”,并非现代意义上带有左倾意味的“激进主义”,而是对权力本身具有彻底约束意味的“激进主义”。作为史官的老子,对于周礼甚或前代诸种礼制的利弊得失,可谓了如指掌。稽诸《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和《礼记·曾子问》等史料,皆载有孔子曾多次“问礼于老子”之史实。或许,正是痛心于对人类社会诸种礼制之流弊及其衰亡残局的历史教训,老子哲学本体论的视角,必然要“突破”并超越所有限制人性“自然”发展的各种礼制,进而直抵能够生育和支配人间万物的终极之源——“道”。老子之“道”,不仅是生育世间万物之“母”,还是支配世间万物存在、发展、甚或衰亡的总规律。老子通过所谓的“道”乃“象帝之先”,从而将夏商两代礼乐文化所崇拜的至上神——“帝”,置于“道”之后;又通过所谓的“道”乃“先天地生”,又将西周本于“敬天礼地”而成的“礼乐文化”降于“道”之下。老子之“道”如此的乾坤大翻转,实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之说。至于由此建构而成的、颠覆性的“哲学的突破”,自当毋庸置疑。正如著名的老庄研究学者陈鼓应所说:“老子是中国哲学之父,中国‘哲学的突破’始于老子。事实上,对于整个中国哲学史,越往下探索,就越会认识到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影响,远超过其他各家。”[3]
可以说,《老子》“五千言”,所论者皆不出于“道”和“德”二字。老子之“道”之“德”,最根本的特征是“自然”与“无为”。所谓“自然”者,乃是自本自根、本自具足、自是其是、自然而然之意;所谓“无为”者,乃是不加施为、放任自化、任其自成之意。究其实,“自然”者,必是“无为”的;“无为”者,亦必是“自然”的。二者实则二而不二,表里为一,皆是“道”与“德”的本性。故而,大凡与“无为”和“自然”相违背的“有为”和“使然”等人事,皆为老子所摒弃。老子之所以西出函谷关隐居,或许正是失望于周礼过犹不及的“有为”而导致的“礼崩乐坏”之残局。
《老子》“德经”首章,即按照由高到低的次序,列出了惊世骇俗的道德谱系:“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老子看来,在“道”“德”“仁”“义”“礼”五者中,只有顺应“无为”原则的“道”和“德”,方堪称之为“上德”;至于“仁”“义”“礼”三者,由于其与“无为”和“自然”相违背,故而皆被归于“下德”之列。尤其是“礼”,更为老子所不齿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如果说,老子由于耳闻目睹“礼崩乐坏”之残局从而唾弃“周礼”,尚属情理之中,但是他将通常被认为是具有普适价值的“仁”亦归于“下德”之列,却常令人匪夷所思甚或诧异不已。
实际上,老子之所以将“仁”归于“下德”之列,大凡概因人间之“仁”,皆有亲疏尊卑之别,这与老子所倡导的无差别的、“无为”的、宽容的“慈”和“不仁”相去甚远。究其实,人间之“仁”必定要以“推己及人”为前提。抑或说,只有“己”之所“仁”也是“人”之所“仁”时,“仁”才能成为“推己及人”的普适价值。但是在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在个性、欲求、好恶等方面是千差万别的。当“己”之所“仁”并非“人”之所“仁”时,“仁”就难以成为“推己及人”的普适价值。或许正是鉴于此,老子倡导“不仁”,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处所谓的“不仁”并非“不爱”,而是倡导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万物齐一,无任何亲疏尊卑之别的“一视同仁”,以任人间万物自然而然,自成其是。
汉代学者杨雄曾言:“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法言·五百》)。杨雄之所以说“史以天占人”,大凡因上古社会的“史官”,大都蜕变于被称为“卜”与“祝”的“巫官”。的确,作为春秋晚期“史官”的老子,在其著成的《道德经》“五千言”中,有诸多由“天”或“道”而推及于“人”的表述。诸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等等。上文所举,都是由“天”或“道”推及于“人”“侯王”和“圣人”等。这足以证明,作为史官的老子有“史以天占人”的学统倾向性。相比之下,孔子一生却“罕言天道”,可谓奉行“尽人事,听天命”之典范。或许,同为史官的司马迁之言,更能彻透老子思想的精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为史官,“通古今之变”当属职业的天职,但是若其学说不能升华为“究天人之际”的哲学高度以俯瞰人间万物,则其“一家之言”或许能够达到“精深”,但却终究会失却“博大”。正如孟子所言:“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可以说,《老子》“五千言”之“哲学的突破”,当属“先立乎其大者”的“道”与“德”。
作为史官的老子,对于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的“古今之变”了如指掌。所谓“礼”者,“序”也;“乐”者,“和”也。三代“制礼作乐”的初衷,本来是要达成人间社会的“秩序和谐”,但是最终却以“礼崩乐坏”而告终。或许,正是鉴于在“以人占天”指导之下“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老子开始转向“以天占人”即“以道观人”,进而建构出“究天人之际”的“道”与“德”,并最终成就其博大精深的“一家之言”。
由“以人占天”还是由“以道观人”作为创设理论学说的切入点,不仅涉及立论所宗的差别,其论据所依和结论所归亦必然旨趣迥然。大凡夏商周三代所沿袭的“礼乐文化”,皆是由“以人占天”的视角而创建的。“以人占天”中的“人”无疑都是世袭的“治者”即“天子”,无论其“德”是否堪以“配天”,他们都是天生注定的“治者”。为了保证“天子”万世一系的世袭地位,“治者”必然要宣告天下其“道统”和“政统”的合法性来源于“以德配天”。其宣扬的“德”,必然是亲疏有别、嫡庶有分和尊卑森严的;由此所制定的封建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礼乐文化”,大凡亦复如此。
若由“以天占人”或曰“以道观人”的视角来看,宇宙自然的大化流行必然体现为天无私照,地无私载,星移斗转,周行不殆;天地万物,乃至人类,无有亲疏,无有尊卑,自然而然,相依共生。或许,正是透过如此“天目”,老子洞见了另一番不同的天地人生,著成了石破天惊的“五千言”——《道德经》。老子如此扭转乾坤的世界观,不亚于哥白尼由“地心说”转向“日心说”的知识革命。故而,若仅局限于“以人占天”的视角解读《老子》一书,或许仅能得其一鳞半爪而已;唯有像老子那样由“以道观人”的高度鸟瞰世间万物乃至于人间社会,方可得其大旨。《老子》一书,其内涵可谓博大精深,其外延可谓无远弗届。自古以来,兵家阅之谓之兵,法家阅之谓之法,师者阅之益传道,王者阅之益于治,仁智各见,无不鉴之而有益。何故?以其“以道观人”之故也;确言之,以其“以道观天地”“以道观人”,“以道观天地万物”的“常道观”,巨细无漏之故也。
就“哲学的突破”而言,老子学说可谓以“道—德”一以贯之的、全方位的、系统的“突破”。诸如,以终极的“道”立论,以超越周礼至高无上的“天”;赋予“道”和“德”以“无为”和“自然”的秉性,以超越周礼“有为”和“使然”的痼疾;以“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将人间之“王”列为“四大”之末,以俾使其自知其上仍有所限所效;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超越当时唯周礼是从的局限;以“不言之教”超越规训的“礼乐教化”甚或儒家的“仁义教化”;以“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开创朴素的“万物平等”和“天赋人权”等观念;以“几于道”的“上善若水”,隐喻人类应该效仿“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奉献精神;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启迪人们不要执着于有德如否,真正的德行乃是自然地流露;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赋予自然万物一视同仁的主体地位,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霸权地位,等等。关于老子学说的“破”与“立”,本书下文的相关章节将有具体涉猎,此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