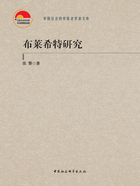
前言
我研究布莱希特,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的魅力就在于他一生是个不墨守成规,颇有创新精神的作家、艺术家。他是德国20世纪剧作家、诗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欧洲“史诗剧”创始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曾经凭借个人魅力,吸引了一批作家、艺术家、哲学家,与他一道构建与时俱进的美学规则。他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尝试借鉴中国元杂剧写作技巧和戏曲表演艺术,突破欧洲传统美学思维,创立了“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学”。从青年时代起,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积极研读中国先秦哲学和历史文献,成为中国文化的知音,作品里充满中国智慧,晚年被人誉为“中国式智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曾与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契一道,影响了整整一代欧美知识分子,引领他们走上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翻译了他的剧本《高加索灰阑记》,这是第一次与布莱希特打交道。紧接着又翻译了他的史诗剧理论《戏剧小工具篇》。此后还陆续翻译了他的一些剧本、诗歌、散文和文学理论著作。选编过一本外国人研究布莱希特的论文集。我的第一篇关于布莱希特的论文,写于1963年,发表于1979年《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为何15年以后才发表?过来人都能理解,那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大家都忙于“反帝”、“批修”、下乡“滚泥巴”,有机会写点批判文章,抑或写点介绍外国文学的赏析性短文,尚可发表,而写布莱希特论文,纯系“贼心不死”,只能藏在抽屉里等待时机,况且还有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那不是做学问的时代。
我研究布莱希特,按照惯例,是从研究一般性问题开始的,比如布莱希特“史诗剧”理论、史诗剧创作与表演艺术、布莱希特“无韵抒情诗”、他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等等。这些最初的研究成果,对于普及布莱希特史诗剧知识,帮助读者理解布莱希特艺术主张,发挥了启蒙作用。不过,从学术角度来说,它们毕竟属于“重复性研究”,当然,其中不乏个人研究的心得和理解。所谓“重复性研究”,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个调查研究过程,先弄清楚前人在这个领域,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有些什么空白点尚待深入探讨。我编选外国人研究布莱希特论文集,做的就是这种调查研究工作。我最初写的那些关于布莱希特的论文、学术性随笔和短评,也是这种调查研究的结果,本书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就是从这部分文字中精选出来的。
我这人,表面看来循规蹈矩,其实骨子里是相当不安分的。文章尚未写几篇,就不再安于重复别人的研究成果,开始琢磨着如何冲破既有藩篱,搞点新玩意儿。天马行空当然可以随心所欲,落实到行动上就没那么容易了。我当时发现,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应该是个不错的课题,那时各国布莱希特研究者,对此关注得不多,中国学术界对这个课题尚处于“不屑一顾”的状况。一位当时颇有成就的布莱希特研究者,认为议论这个问题,纯属“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我国学术界刚刚有人议论布莱希特的“中国情结”,便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我虽然意识到这个课题的重要性,可我在知识方面先天不足,对布莱希特曾经关心过的中国文化现象,除了对他所说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并非完全无知之外,我对中国唐诗、元代杂剧所知甚少,尤其是在先秦哲学方面,除了知道某些人名、书名,几乎是一张白纸。我当时的知识水平,无法应对这个课题,只好一边继续写重复性文章,一边摸索出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巴巴拉·考尔巴赫的德国女汉学家来北京访问,邀我随便谈谈。她回国以后给我复印了一部韩国学者写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布莱希特与东方文化的关系。其中谈到布莱希特戏剧创作的蓝本问题,他说唯独《四川好人》蓝本问题至今未搞清楚。我注意到,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成为我研究布莱希特的突破点。从此我在阅读中注意朝这个方向搜集和积累资料。有一次我在德国学者维尔纳·密滕茨威《布莱希特传》里,发现了布莱希特最初拟定的《四川好人》创作提纲,我发现这个提纲的内容,与元杂剧关汉卿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剧情十分吻合。这个发现让我激动了好几天,那时我常常想,当年伽利略发现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时候,大概也会激动成这副样子,这不就是发现新事物的乐趣吗!
从此我盯上了这个课题,一定要把别人未弄清楚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并由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蹚出一条新路。为此我下定决心中断正在进行的课题,花十年时间补上中国古代哲学这一课。好在当时书店里出现了许多先秦哲学译注本,为我这样对古代汉语一窍不通的人提供了方便。我弄到手的第一本书,是“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墨子全译》,后来又弄到《庄子全译》《道德经·南华经》译注本等。说也奇怪,进入这片新天地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越读越觉得自己无知,于是从来不敢阅读的《道德经》《周易》《尚书》《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列子》等,囫囵吞枣,读得爱不释手。我逐渐弄明白,为何布莱希特那么喜欢中国古代哲学,原来这片天地,竟是那么辽阔广大,精湛深邃,绚丽多姿,魅力无穷啊。
眼看我已进入古稀之年,尽管书读得津津有味,可我并未乐不思蜀,我的初衷毕竟是研究布莱希特。我遵循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个方向,撰写的第一篇论文是《“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传统》,发表在2004年的《外国文学评论》上。这篇论文堪称“十年磨一剑”。该文不仅按照原来设想,首次回答了《四川好人》的蓝本问题,还重点论证了布莱希特如何吸纳中国元杂剧剧本构成元素,形成史诗剧的结构特点。以如此明确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在布莱希特史诗剧研究领域,还是第一次。这篇论文被刊物主编盛宁先生称赞为“材料之翔实,义理之缜密,令人拍案叫绝”。这个评语给了我很大鼓励,让我有进无退。这篇论文随即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文学研究》(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上,一时之间,我的邮箱差点儿被海内外约稿信、翻译广告挤爆。
从此以后,我的精力主要用于研究布莱希特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我发现自己读了一些先秦哲学,真的如同掌握了一把钥匙,可以用来打开布莱希特的百宝箱了。重读他的作品,无论是剧本、诗歌、散文,还是理论著作,虽然还是那些文本,却有了旧貌换新颜的感觉。难怪德国人说,不懂中国哲学,很难真正理解布莱希特的作品。从前读他的诗歌《题一座中国茶树根雕狮子》,只是觉得作者文字的运用,精练到令人折服的程度。读过《列子》以后,你会发现该诗前两行:“坏人畏惧你的利爪,/好人喜欢你的优美”,正是套用了《列子·杨朱篇》中“善者服其化,恶者畏其禁”两句话。连主语、谓语都不差分毫。当你联想到子产相郑三年,国泰民安,诸侯不敢侵犯时,你会觉得这首诗的立意,是多么深远与高大啊。我在阅读另一首标题为《1940》的诗时,眼前立马浮现出“学,以为不知‘学之无益’也,故告之也,是使知‘学之无益’也,是教也,以学为无益也教,悖”。这是《墨子·经说下》中的一句语录。作者袭用墨子讨论“逻辑悖论”的文字,以父子对话形式,表现了自己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严峻形势,内心的忧虑和乐观主义信念。类似的发现越来越多,我也不再像当初发现《四川好人》的蓝本那样激动了。例如我还发现《伽利略传》中的伽利略,遭到宗教裁判所软禁,撰写《两种科学体系的对话》,多么像“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的周文王,被殷商囚羑里而演八卦的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的主人公,他在德国纳粹面前装疯卖傻,口无遮拦,常令侵略者陷于尴尬境地,令人想到这不就是“佯狂披发,以晦其明”的箕子的变形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当我意识到布莱希特把《易经》原来的德文标题,从“Buch der Wandlungen”改译成“Buch der Wendungen”时,我的第一反应,何止是激动,简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一字之差,表现了他对《易经》真谛的理解。原来在他看来,《易经》的真谛不只是“变易”,它的更深层次含义是“转变”。用中国话来说,是“物极必反”。用欧洲哲学术语来说,就是从“量变”到“质变”。试想从“乾卦”到“坤卦”、从“泰卦”到“否卦”、从“损卦”到“益卦”、从“既济”到“未济”,不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吗?布莱希特真正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居然能把东方人与西方人,古代人与现代人的思想材料,融会得如此贯通,理解得如此出神入化。你不能不佩服他。联想到他晚年那种中国式的谦和善良,虚怀若谷,宽容大度的为人处世态度,我常常想,布莱希特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伟大知音。我这样解释他,兴许有人会说,这是“捕风捉影”。我不会怪罪任何人,因为这是我的理解,见仁见智嘛。说实在的,我与丁扬忠先生在布莱希特研究这方舞台上,“二人转”唱得太久了,好想有新人参与进来,给这个领域增添生机。
布莱希特一生写过不少语录式散文,其形式类似孔子的《论语》。德国浪漫派时期的领军人物,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一生写过上万条类似的语录,表达他的哲学、文艺学思想。德语称这类“语录”为“Fragment”,我国学者陈恕林先生在他的《论德国浪漫派》中,把它翻译成“断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出版家和学者,把布莱希特写的这些语录式散文,编辑在一起出版时,取名为《墨子/易经》。如今成了世界各国布莱希特爱好者,借以了解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关系的一个窗口。我在阅读这些语录时,逐渐萌生一个想法,何不采用中国学术界熟悉的研究古代文献的译注法,来解释布莱希特的作品呢?近年来我做了些尝试,其中的一篇收在本书第一辑里,与本书其他文字一起,企望得到学术界同仁指正。
2017年2月23日,记于车公庄坎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