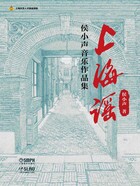
七 难忘三年连办三届通俗歌曲大赛
中国港台地区流行歌曲好听,但也有格调不高的作品。中国大陆怎么办?音乐界的责任是什么?——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音乐界几乎天天在议论的话题。1985年夏,我这个刚刚走上市群众艺术馆领导岗位的音乐人,与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包括《解放日报》等三大报)以及企业界的一批朋友们,连续组织了面向全国征稿的上海三届通俗歌曲创作、演唱比赛。
当年的文化局、广电局非常支持这一活动,迅速批复,列为官办。然而毕竟开放伊始,政策上的事还常在观望,不易把握。记得首届大赛序幕拉开不久,文化局说,宣传力度和尺度问题,还是看看中央吧。赛事“搁浅”了一个多月,才比较放心地关照我们“继续进行”。关于唱法分类、歌种定名也有争议,究竟叫“流行歌曲”“轻歌曲”还是“通俗歌曲”?最后,我们尊重音乐理论家谭冰若的建议,统一称“通俗歌曲”,这一称谓在业内一直沿用至今。首届比赛应该是中国各省市级政府主管部门主办的同类大赛的第一次,即首创。它有风险,有新意,也颇具吸引力!
创作型的大赛凝聚了各地优秀词曲作家的心。北京的谷建芬、付林来稿了,沈阳的铁源来稿了,中国香港地区的黄霑(《我的中国心》作曲)在郑南鼓动下也来稿了。当年的“少壮派”人物孟庆云每届都送稿上门,徐沛东则挤上了第三届这辆“末班车”。当然,上海参赛人数居多。经评选,《月亮走,我也走》《思念》《小城有一支歌》《别亦难》《我热恋的故乡》等一批佳作从大赛中脱颖而出,经演唱新作的磨合,肖雅、周冰倩、周海平、纪晓兰等一批新秀从大赛走进了观众的视线。
这三届通俗歌曲大赛,让我领略了去寓所约稿之时,老一辈作曲家姜春阳作为共勉金句的“要跟上时代步伐,至少不要挡道”之真谛,也使我悟出了“高格调,新手法,浓色彩”那聊以自勉、同时也让曲友们记住了的九字要诀。
难忘颁奖活动中的采风时刻,歌剧《江姐》作曲姜春阳拉着我同唱一曲《红梅赞》;
难忘大赛推出的《难忘今宵》已被中央电视台用作每届春晚必唱的主题歌,成了传世之作;
难忘三年来我们连续三届执着地举办通俗歌曲创作、演唱大赛,吃了“第一只螃蟹”,成就了音乐界一段交口称赞的历史,成为中年以上音乐爱好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也难忘本人参赛作品《黄土路》有幸在匿名评分中列入一等奖行列。因自己系组委会工作人员的缘故,我执意把它降到二等奖。这一情节应该鲜为人知。
被我自己称作“抓了西北风尾巴”的这首《黄土路》在当时传唱度、选唱率达到相当量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在《广播歌选》期刊“听众喜爱的歌”栏目中专题推介。
见乐谱卷《黄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