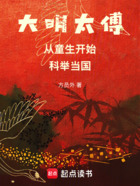
第11章 童生讲书
李知县笑眯眯地望着方原:“方生于《书经》内,可有熟悉的篇章?”
方原朝李知县一礼:“小子不敢言熟谙经义,但也勉强通晓一二,县尊大可任选一节,小子试讲之。”
“好!”李知县赞赏道,“少年人合该有此意气!既如此,你便讲讲《旅獒》一篇吧。”
方原心中一顿,这李知县到底是科班出身,挺会出题的嘛!
《旅獒》是劝导君王的名篇,童生即便不以《书》为本经,也是必学的,只要是好学的童生,都能讲出个七七八八。
但也基于此,讲通他容易,讲好他却难。
照本宣科,老生常谈之语,最多令李知县颔首,说个“甚好”,却绝不会击节赞叹,视为可堪爱护的好苗子。
这不是方原想要的效果。
科举时代,一个有才名且被父母官中意的童生,虽不一定能中举,但却一定能入县学成为秀才,不然本县老爷的脸面何在?
所以,方原此次讲书需讲得晓畅明白且有新意,才能赢得知县的青睐,这对之后科举大有裨益!
思忖片刻,方原朗声道:“旅獒者,西夷旅国之大犬。”
李知县面无表情,此句是照搬注解,听不出好坏。
“昔周武王时,有西旅国,以本地所出獒犬,进献于朝。太保召公,以为异物非所当受,作书进戒,遂以旅獒名篇。”
这是解释了此篇来历,也不过老生常谈,李知县有些失望,但想想也对,方原毕竟是个小童生,能做到如此已是不错,不必期望太高。
可接下来一句,却令李知县眼中精光一闪。
只听方原道:“此篇主意自在慎德二字。自古明哲之王,欲以保国治民,莫不谨修其德,凡一取一予,一喜一好,皆兢兢然以道理自防,法度自检,无所不致其谨。”
竟然是从慎德发论,有点意思。
李知县点了点头,继续倾听。
方原顿了顿,放慢语调:“既言德之慎也,便不敢存狎侮之心,不敢从耳目之欲!是以远迩之交无所忽易,不以蛮夷为可轻;方物之贡不尚珍奇,不以远物为可宝,盖慎微之至也!昔纣王初立,食用象箸,箕子哀叹,称此以求,天下不足矣!后果不其然,造鹿台,为琼室玉门,酒池肉林,宫中九市,而百姓皆叛。此见微知著也!”
哎呀!
李知县忍不住赞声道:“慎德应慎在细微处,正当如是啊!”
方原不骄不嗔,继续道:“慎德之至则德盛,则自不狎侮,而以礼接人,不以远人忽之,致启宠纳侮也。苟其有所狎侮,则君子必有离心,小民必怠于力,无以服人而为德盛之玷矣!”
这是言慎德容易被狎侮(轻慢)毁掉,字字珠玑,铿锵有力,直击李知县心神!
诸童生早已对方原麻木,虽听不太懂,但觉得厉害就对了!
李知县频频颔首,拊掌对吴先生道:“此言振聋发聩,直解其味,甚佳!甚佳!”
吴先生也感慨道:“此子对经义一道一点就通,我虽为先生,教他习经,却也受益良多。”
李知县又道:“方原你很不错,不过本县再问你,《旅獒》篇中有一句‘不役耳目,百度惟贞’,我若让你来解,你可能解出?”
方原在心里暗暗吐槽:“你都让我来解了,我敢说不能吗?”
“小子可试着一解。”
方原思考了片刻才缓缓道:“人心之应事接物,本都有个至正的节度。若为声色之欲,感于耳目,心无所主,反为耳目役使,于是百为之度,始昏乱而失正耳。是故君子澹然无欲,卓然自持,耳目皆听命于心,不为玩好役使,则私欲不行,百事为之,自然合于节度,而各得其正。”
李知县哈哈一笑:“没成想今日视察社学,还让本县发掘个麒麟儿来!不虚此行!不虚此行!”
一旁的礼房老吏呵呵笑道:“恭喜县尊,贺喜县尊,在您治下出了此等神童,可见县尊教化之功!”
一县政绩,一在赋税,一在教化。
对李知县来说,余杭治下出现如此聪慧少年,简直如同地里长出嘉禾一般,假以时日养育成材,与他官声将有极大助益。
李知县闻言心中大乐,脸上都快笑出花来。
“方原,今后你要好生向学,本县可是对你寄予厚望!”
方原一揖道:“学生敢不从命!”
从“小子”换成“学生”,方原也懂得顺杆子往上爬。
李知县乐得如此,心情大好之下,便问吴先生:“学校有什么困难,大可向本县倾诉。”
吴先生心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思索片刻道:“此间社学原是淫祠改建,学田也承继庙产,仅有薄田五亩,日常开支、资助贫童完全入不敷出,童生中有许多人连书本都不能齐备,实在令晚生心痛,求县尊再拨些学田,以纾学校之困。”
社学在国初原本是官办,但地方官的德行可不敢恭维,硬生生将学校办成了敛财之所,让明太祖朱元璋大为恼火,还感慨好事难成,最后诏令民间自办,不许官府干涉。
但好景不长,没了官府干涉,地方社学虽兴盛了一段时间,又开始逐年荒废。
正统初年,英宗皇帝又令各处提学官、地方守令严督社学,不许废弛,社学这才又回归公办道路,可办学经费朝廷从来没有专项开支,得当地官员自筹。
于是有条件的就新建社学,没条件的则利用废弃的寺庙、官廨,捣毁的淫祠改建校舍,而教师的工资、学校日常养护、开销,以及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则都从学田收益出。
只不过头疼的是社学众多,而官府充作学田的土地有限,分拨下去就没多少田亩,养活教师都费力,何谈其他。
李知县看着学堂内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有些童生衣衫上还打着补丁,三人挨在一起,面前木板案上却只有一本书。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李知县转头唤道:“冯司吏。”
礼房老吏,忙躬身应承:“县尊有何吩咐。”
“你回去查阅下田籍,若有可堪使用的官地,分润几亩出来充作社学之田。”
老吏略有迟疑,随即称是。
吴先生一揖长拜:“晚生谢过县尊大德!”
童生们也跟着有样学样:“谢过县尊大德。”
李知县捋须微笑,老怀大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