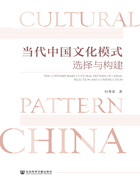
二 文化模式
“文化是一种习惯,或至少得以习惯为前提。”[17]习惯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存在。在笔者打出这句话时,笔者所使用的QWERTY(以该键盘上最开头的几个字母顺序命名)标准打字机键盘字母的排列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QWERTY键盘设计于1874年,其字母的排列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当时打字机的字块之间的相互干扰。但是,标准打字机键盘也有一些严重的缺陷,特别是在标准打字机键盘上只有32%的敲击打在主排(倒数第二排),52%的打在上排,16%的打在下排,而且还要求过度使用比较弱的左手以及最弱的小手指。58年后的1932年,美国生理学家奥古斯特·德沃夏克发明了一种能够克服标准打字机键盘缺陷的键盘。多次测试一致表明,学会德沃夏克键盘的时间是学会标准打字机键盘时间的三分之一,打字员一旦学会操作这种键盘,准确率可以提高68%,速度能够提高74%,而且明显减少了疲劳感。[18]尽管如此,时至2019年的今天,我们仍在使用“不合理”的标准打字机键盘,而对德沃夏克键盘置若罔闻。尽管德沃夏克键盘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优于标准打字机键盘,但因为标准打字机键盘享有的先行优势已经使其从19世纪走进了21世纪。这种所谓的“先行优势”其实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一种喜好“定势”,包括制造商、打字员、教师、销售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都已经“忠于”旧的键盘,这种“忠诚”形成了对旧有键盘的喜好“定势”。有时,改变这种“定势”并非易事,但这种“定势”并非不可改变。新旧文化模式的形成与转换也往往要经过屡次诸如此类的、极其艰难的冲突与蜕变才能实现。这种“定势”与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自然科学“范式”这一概念比较相似,用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概念来说,就是“文化模式”。
何谓“文化模式”?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认为,文化模式是指一种文化的结构和功能;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模式是相对于个体行为而言的,具有主体选择性的普遍社会价值取向,文化模式不仅体现了文化的差异,而且塑造着各自所辖的那些个体。她认为:“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19]克鲁伯和本尼迪克特关于“文化模式”理解的共识在于承认存在文化模式,且文化模式对文化和处于其中的人起着重要的形塑作用。综合来看,文化模式是指某种文化具有的稳定的、普遍的特征与样式。“文化模式”以整体的方式呈现,个体日常生活是其主要载体,文化模式的转型会对个体日常生活带来直接影响。
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记述了一位谦恭的印第安老人面对生活的巨大改变时所说的充满悲情而无奈的一句话:“现在我们的杯子破碎了,没有了。”这里的“杯子”,其实就是他们生活中原有的那种生活样式与生存意义,它承载着包括衣食起居在内的生存与生产方式。与其说是因为这只“杯子”破碎了,人们的生活才发生了巨大改变,不如说是因为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这只“杯子”才破碎了。而正是人们的生活与“杯子”的双重改变,进一步推动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礼仪规范以及是非标准的巨大变化,进而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变迁甚至转型。尽管如此,文化的某些重要“碎片”仍会顽强地残存于新文化之中,或者说,残存于印第安老人心中的“杯子”的“碎片”并不能完全被人主观地抛弃。因为这些“碎片”已经深深地刻入身处其中的每个成员的认知与行为中,虽然它已经不再以显性的方式表现自己,但它一定是组成未来文化的不能缺席的因子。这位印第安老人的话,表达了身处文化转型中的人们面对文化模式转型时的无奈以及接受文化转型的艰辛与痛苦。对传统社会中的人而言,对传统生活样式的每一次改变和否定可能是“灾难”,也可能是“涅槃”,而文化发展则往往体现在旧的文化模式被颠覆或被超越的过程中,这就是文化模式的形成与转型。
文化模式的形成与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按本尼迪克特的理论来理解,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总会形成某些相对稳定、普遍的东西。正如作为个体的人在成长过程中,总会有相对稳定、较为持久的生活习惯与处事方式一样,处于漫长历史变化中的文化也会逐渐沉淀为某种相对稳定的特征与样式,即文化模式。就某一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而言,其总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些相对稳定的模式。如尽管引起较大争议却也受到普遍认可的本尼迪克特对日本“菊与刀”文化模式的概括,以及现代日本文化在大量摄取美国文化后形成的“和魂美才”模式,美国文化所形成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的“拼盘、杂交或熔炉”模式等。随着社会生活向前推进,这些固有的文化模式也一直处于不断更新与演进之中。当我们谈到某种固有的文化模式时,文化模式已然存在,而当我们说打破固有的文化模式时,就是力图对旧的文化模式予以“解构”,经过推陈出新、重新选择而逐渐建构新的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确立与更替的过程也是文化范式建立与转换的过程,范式的转换是种革命。“范式”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谈到科学革命时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库恩指出,科学的发展总会经过“前范式科学—常规科学—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的范式转换过程,即在竞争中建立范式,在反常与危机的挑战中既有的范式发生动摇,再经过竞争与选择建立新范式,开启新常规科学。正是在这种“范式”的形成与转换过程中,科学发展了。相应的,文化范式的建立与转换过程既是文化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化模式生成与变化的进程。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推进,文化模式也将处于不断生成、变化之中。文化模式的发展过程一般会经历形成期—稳固期—调整期三个阶段。处于形成期的文化模式体现为文化主体自发或自觉地选择与构建文化模式,并形成多种模式之间的文化互动,这种互动在性质上有积极与消极两种可能。处于稳固期的文化模式往往会形成或呈现为“文化定势”,可能会对文化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束缚文化的发展,从而陷入文化循环;二是形成新旧文化模式之间的“文化冲突”,或阻碍或推进文化发展;三是通过主动地利用其积极作用,减少其消极影响,进而形成突破消极文化定势的进步力量,然后开始进入文化模式的调整期。处于调整期的文化模式则要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采取被动或主动的方式推进文化模式转型,这是新一轮文化模式的选择与构建。文化模式形成的根源与动力是人们的生产及生活实践。同时,文化模式一旦形成,也会对处于其中的人及其生产、生活、观念等产生巨大影响。走出文化循环论,破除新旧文化模式之间的“文化冲突”,推动文化模式转型需要加强文化自觉,特别是文化模式选择与构建的自觉。
文化模式对生活于其中的人有强烈的影响与塑造作用。一般来说,人们会把接受其影响与塑造的人视为“正常”的,而把与其所处的文化模式有巨大分歧的人视为“反常”的。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具体谈到了三种文化模式:阿波罗型(日神型)、狄奥尼斯型(酒神型)与妄想狂型。本尼迪克特指出,美国西南部的普埃布罗文化属于阿波罗型,其节制、热衷礼仪以及将个性淹没于社会之中,具有中庸节制的特点;温哥华岛上的夸扣特尔文化则是狄奥尼斯型,其偏爱个人竞争对抗,嗜好心醉神迷,好幻想,具有好出格的特点;美拉尼西亚的多布人则是妄想狂型,他们严厉冷酷、一本正经、感情冲动,具有好嫉妒、猜疑和仇视他人的特点。她认为,文化的作用导致不同的文化模式形成,生活于某种文化模式中的人必然会受其影响。本尼迪克特认为,自身的性格与其生长的社会文化性格吻合的人是十分幸运的,而生长在酒神型文化中的具有日神型性格的人,或生长在日神型文化中的具有酒神型性格的人则往往被视为文化的“越轨者”或“异常者”。在某个社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在另一个社会可能被视为非正常,反之亦然。所以,她主张对具有特殊行为的人采取宽容态度,鼓励个体差异,允许个人有较多的文化偏离。[20]可以说,在一个社会中占主流与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易于接纳共性,却天然排斥个性。由是观之,文化模式的选择与构建会影响身处其中的个体的生活方式乃至价值判断,易于形成社会的文化合力,并汇集成维持某种社会秩序的无形力量。同时,文化模式一旦固定下来,又容易形成对个性、新事物的排斥,进而形成排除异己的力量而阻碍文化与社会的创新与进步,形成对人类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文化模式的作用有积极之处,也有消极之处,研究文化模式就是要正视其客观性与现实性,在文化模式形成、稳固与调整的不同时期充分发挥文化模式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