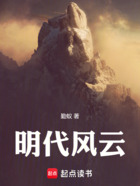
第45章 朕知道了
望着太子殿下坚毅的神情,商辂默默点了点头。
他与于谦共事也有一段时日,心知这位于大人性格刚直,看到那些懦弱的大臣、皇亲贵族,总会曾心生鄙夷之情。
每遇工作受阻,便常听到他拍案长叹:“这一腔热血,不知何时才能报效家国!”
念及此处,商辂不禁暗自祈祷:但愿这位忠心耿耿的国之栋梁,千万不要一时糊涂走上歧路,否则必将祸及天下苍生。
朱齐并未察觉商辂的思绪,他正专注地翻阅着手中的卷宗。
每看到一个名字,他都会在心中默念,试图触发那神秘的预警能力。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始终一无所获。
“待闲暇时,定要将这宫中上下所有人的名字都试一遍。”
朱齐暗自咬牙,“有了这预警能力,任你藏得再深,也休想逃过我的眼睛!“
但一想到先前乱入的画面——这宫中如此多的后妃宫女,朱齐不禁直冒冷汗。
“嗯!定要寻个合适时机!”他心中想道。
商辂不知太子心中所想,又从袖中取出一份文书:
“殿下,北城兵马司今晨呈报,发现一名宦官暴毙于住所。据现场遗留身份符牌显示,这名宦官名叫张喜,系中毒身亡!”
“张喜?”朱齐想起那名董平见过一眼的神秘宦官,先前视频预警之中已经显示他倒地身亡,这个线索如今已经是断了。
虽然早有预料,他还是追问道:“可查出是何人所为?”
“据走访周边,无人目击到可疑之人出现。”商辂摇头道,因这张喜之死与太子安危无直接关联,他并未深究。
只是近日接二连三的离奇案件让他倍感压力,便随口问道:“不知殿下是从何处得知张喜死讯的?”
此言一出,朱齐顿时语塞。
难道要告诉商辂,自己是靠神奇的预警能力得知这紫禁城外发生之事?
这说法未免太过荒谬,商辂只怕是会认为他疯癫了。
就在他踌躇之际,商辂敏锐地察觉到太子的异常,心中暗叫不好:莫非此事与殿下有关?
正当商辂懊悔自己失言时,朱齐急中生智:“额...这乃是董平听周边宫人议论所说,想来不会有假。”
已经依照太子所言,在放掉两名刺客后,此时正在宫外闲逛的董平突然打了个寒颤,裹紧衣衫嘟囔道:“这天儿太阳正好,怎么突然又冷了?”
见商辂将信将疑,朱齐连忙转移话题:“对了,昨日清单上的物品,先生可都置备齐全了?”
“都是些寻常物件,只是那天然硇砂着实难寻。”商辂虽公务繁忙,却也将太子的嘱托办妥,
“因购置数量较多,不便带入宫中。殿下今日午后不是要去西苑习射?届时臣再安排人手转交。”
商辂不知道殿下买这些东西是何用意,他那份物品清单中含有大量的水果,还有这天然硇砂。
《本草经集注》虽载,这天然硇砂可“消积软坚、治疗痈肿、噎膈等疾病”,但观太子气色康健,不似患病之人。
思来想去,能用上这等药材的,恐怕只有……
“那个刘六儿伤势如何了?”商辂突然问道。
作为锦衣卫指挥使,他只在案卷记录上看到前日这名东宫侍卫为太子挡刀的记录。
“说恢复得不错,如今在太医署好生养着,只是整日嚷着要回来当值呢!”
提起刘六儿,朱齐眼中闪过一丝感激。
那日若非这侍卫奋不顾身挡下致命一刀,即便有视频预警也未必来得及反应。
商辂捋须而笑,眼中精光闪动:“既然伤势已无大碍,这等忠勇之士,殿下出巡时不妨带在身边。一来可彰其功,二来也多一分周全。”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道:“近来风波不断,多一个心腹护卫总是好的。”
“正合我意!”朱齐闻言朗声大笑,“既然这家伙已无大碍,明日便召他回来当值!江昊那几个小子,可是眼红他在太医院躺着享福多日了。”
商辂躬身应是,心中已在盘算如何为刘六儿邀功。
《大明会典·兵部》明确规定:“凡武职袭替、升授、降调,皆由兵部拟注,请旨定夺。”
按常例,刘六儿这等护驾之功,擢升个小旗本是理所应当。
“殿下,”想到这,商辂略一欠身,谨慎进言,“臣斗胆提议,不如先授刘六儿'东宫侍卫统领'之职,权作临时差遣。
待臣具本上奏,经兵部武选司核查其功过后,再请陛下明旨定夺。
想来以圣上对殿下的爱护,必不会在此等小事上为难。”
“先生此议甚妥,便依此办理。”
朱齐微微颔首,眼中闪过一丝深思。
身为储君,若亲自为麾下武将邀功请赏,难免会落人口实——朝中那些言官少不得要参他在宫中“结党营私”“培植羽翼”。
更何况如今景泰帝虽对他信任有加,但帝王心思最难揣测,这等敏感之事,还是由锦衣卫指挥使出面更为妥当。
念及此,朱齐不禁暗自庆幸。
那日力荐商辂执掌锦衣卫,当真是步妙棋。
此人既忠心耿耿,又深谙朝堂规矩,更难得的是处事圆融老练,正可为他分忧解难。
“举荐商辂为指挥使……是不是更容易被言官御史诟病呢?”朱齐忽然想起这事,心中多了几分犹豫。
-----------------
不等朱齐犹豫,那些弹劾太子“结党营私”的奏本已经摆在了景泰帝的桌上。
“臣监察御史钟同、吏部尚书王直谨奏:
窃见太子身为储君,宜持重守静,以彰圣德。
然近日访得,其与锦衣卫指挥使商辂往来甚密,文书频传,暗通款曲,殊失储君之体。
查商辂执掌锦衣卫,权柄甚重。
凡所行之事,皆关朝廷机密。
今与东宫过从甚密,恐有勾连之嫌。虽未见其显迹,然:
一、商辂屡赴东宫奏事,而外廷大臣不得预闻,事多隐秘;
二、近日锦衣卫调阅兵部东宫侍卫档案被焚,而商辂不严查,反与太子暗议,恐有掩蔽之情。
故,太子潜结近臣,交通禁卫,此非结党而何?
虽无实据,然形迹可疑,不可不察。
伏乞陛下:
敕令太子慎守本分,勿与外臣私相往来;
下锦衣卫指挥使商辂于法司问状,以明心迹;
彻查东宫与锦衣卫文书往来,以绝隐忧。
储位关乎国本,岂容私相授受?臣职在言路,不敢不言,伏惟圣鉴。”
“简直胡闹!”景泰帝眉头深锁,望着御案上这本奏折——太子行事竟如此不谨,徒留话柄于外臣,着实令人失望。
目光扫过奏疏上联署的“王直“二字,他脸上恼怒之色变得更多了:
“监察御史风闻奏事是本分,你一个吏部尚书也来凑什么热闹?
去岁易储之事,这王直便屡屡作梗。
忆及当日,思明土司知府黄矰上表请易储君,正合朕意。
命礼部集议时,当时满朝文武九十一人皆署名附议,唯这王直面有难色。
若非陈循强执其手连署,险些坏了大事。
后来朕念其才学,欲加太子太师之衔以示恩宠,此人竟当殿顿足叹愧。
致使朕的东宫只有太子三少(注:少师、少傅、少保),太子三师之位却是空悬至今。”
突然,景泰帝冷哼一声,似乎是想通了什么:
“太子所为,不过因遇刺受惊,举荐商辂为锦衣卫指挥使也是为求自保。
这老匹夫竟急不可耐上疏弹劾,未免欺人太甚!
朕虽知储君确需约束,然王直此举,究竟是为国尽忠,还是挟私报复?”
想到这里,景泰帝下定决心,将这个奏折留中不发。
但涉及到东宫,为了避免司礼监过度揣测,只见他提起朱笔,在奏折上飞快地写了几个字:
“知道了,暂且留中,朕自有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