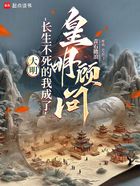
第52章 你可是欲改皇明之根基?
徐良目光坚定,毫不退让:“所以才需‘完善评价,去伪存真。’”
他伸出第四根手指:“科学不同于旧学,不能凭名望定高低,不能因学者之身份而断其是非。唯有试验、数据,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姚广孝微微点头,叹道:“此言甚是。”
“学术若无客观衡量,只凭师承权威,便易陷入盲从。”
朱高炽若有所思:“先生可有例证?”
徐良轻笑,抬眸道:“宋时沈括,曾著《梦溪笔谈》,其中便有一例。”
他缓缓放下茶盏,正色道:“自古以来,学者多言地震乃‘天人感应’,谓之帝王失德,天降示警。此言一出,士林皆附和,谁敢置喙?”
“可沈括不同,他亲自考察地震发生之地,察看山川起伏,最终得出结论——地震并非神谴,而是地壳自身的运动。”
“此说一出,士林大哗,众人斥之‘异端’,然则事实如何?今日之天下,已无人再言地震乃帝王失德所致。”
“若沈括亦如旧学之人,只知盲信古籍,不去求证,那这谬误,怕是要再流传千百年。”
朱棣深深看了徐良一眼,缓缓道:“此事孤曾听闻。”
姚广孝捻着佛珠,轻叹道:“以往凡遇地震,朝廷即遣官祭天,修德祈福,却不曾想过其中原理。沈括之言,正是‘格物致知’之道。”
徐良郑重点头:“这便是科学精神——不以人言为是,不以师承为尊,而是以天地万物之理为据。”
“此风不立,天下学问便终究是浮沙筑台。”
朱高炽若有所悟,缓缓道:“如此说来,先生欲立新学之法,正是要让士林明白,学问不应固守前人之言,而应自求其证?”
徐良笑道:“正是如此。”
徐良继续伸出第五根手指:“其五,利用合理的工具、书籍,提升传播效率。”
朱高炽若有所思:“先生可有具体之法?”
徐良笑道:“现如今,雕版印刷虽已广泛应用,但书籍仍难普及。若能改进印刷术,使书籍成本更低,便可让学问传播得更快、更远。”
“此外,绘制详细的图谱、编写简明易懂的书籍,也能让更多人学得此道。”
朱棣低沉道:“此法虽好,然则即便书籍易得,百姓未必愿学。”
徐良闻言,嘴角微微扬起,抬起第六根手指:“其六,家国共进,普及于民。”
姚广孝神色微动:“此话怎讲?”
徐良缓缓道:“若科学之道仅在王府、军中流传,那便不过是少数人的技艺,无法真正改变天下。”
“唯有让百姓皆知,使耕者懂农学,工匠知匠术,医者习医理,商贾晓算学,方能真正富国强民。”
朱高炽目光大亮,身子微微前倾,沉声道:“让天下学问,不止为士人所学,而应为万民所用?”
徐良目光如炬,郑重地点头:“当学问只为士人所学,天下便只有仕途一条正道,百姓只能仰望读书人。”
“可若天下学问为万民所用,则士农工商皆可得其利,各行各业皆可精进。”
“如此,皇明方能真正兴盛,远胜于祖制。”
朱棣深深地望着徐良,屋内气氛凝重。
姚广孝忽然低声念诵佛号:“阿弥陀佛。”
他目光幽深,沉吟道:“此言既惊世骇俗,亦深具远见。”
“然则,此举恐将动摇士人的根基,甚至惹得天下文官大哗?”
朱棣冷哼一声,嗓音透着一丝不耐:“文官大哗又如何?太祖皇考扫除权贵、开科取士,本王父子今日尚能坐于此,岂是靠文官恩赐?”
“不错。”
徐良轻笑,端起桌上的茶杯,悠然抿了一口:“文官既是朝廷骨干,亦是固守旧制之人。”
“若不逐步引导,他们断不会轻易接受这些新学。”
“但这恰恰是格物书院的使命之一——不仅要传播新知,更要让天下士人明白,科学之道与儒学并非相悖,而是相辅相成。”
朱高炽眼神闪动,低声道:“此言何解?”
徐良缓缓放下酒杯,正色道:“儒家之道,以治国平天下为本。”
“科学之学,乃求真求实,探索天地之理。”
“二者并行,方能真正造福天下。”
“举个例子——”
徐良抬起一根手指:“《周礼》中有云:‘地可度也,天可象也,数可推也,物可志也。’这便是科学的雏形。”
他又笑道:“孔圣人曾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正是格物致知的精神。”
“若文官明白这一点,岂能拒科学于千里之外?”
姚广孝微微颔首,若有所思。
朱棣听罢,轻哼一声,眼神透着几分审视:“听起来,你这‘格物书院’倒是胸怀天下,想做大事。”
“但问题在于,若士人拒绝,民间恐怕更难接受。”
徐良微微一笑:“殿下可知,民间为何难以接受?”
朱棣皱眉:“为何?”
“因为他们没得选。”
徐良语气平静,却一针见血,“千年来,读书人只认科举,商贾只重利润,农民世代务农,匠人传承技艺。”
“所有人的命运,皆被既定的规矩束缚。”
他微微顿了顿,眼神明亮:“但若给他们选择呢?”
“让百姓知道,他们可以学一门技艺,亦可精研一门学问,而不必再唯科举为尊——殿下以为,他们会作何选择?”
朱高炽深思片刻,缓缓道:“自然会有人愿意尝试。”
“正是!”徐良眼神犀利,“而一旦有人尝试,并因此获得更好的生活,便会有第二人、第三人,直至这条路不再是冷门之道,而成了天下皆知的正道!”
朱棣沉默不语,眉宇微皱。
“再者,殿下可曾想过,皇明欲行远路,单靠武力并不可持续?”徐良语气稍缓。
朱棣捏紧手中的酒杯,眉峰微蹙,目光深沉。
徐良此言,触及了他内心深处的疑虑。
靖难方兴未艾,他虽夺取北平,然天下未定,眼下之计,理当招兵买马,积蓄实力,而非谈及什么“行远路”。
可偏偏,这个“徐疯子”却总能在他意料之外抛出惊世骇俗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