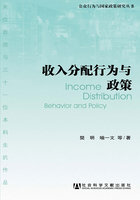
第二节 奴隶社会的收入分配
奴隶社会以奴隶主占有奴隶的人身、实行超经济奴役为主要特征。奴隶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极为不公平的。奴隶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并占有奴隶本身。不少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对奴隶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可随意奴役、买卖甚至杀害。奴隶的后代也世代为奴。被剥夺一切权利的奴隶,无人身自由,被强迫从事紧张、繁重的劳动。奴隶主尽可能多地占有奴隶的劳动成果,分配给奴隶的主要是为维持其劳动力的再生产。
古代最典型的奴隶制是罗马帝国的奴隶制。此外,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战国以前的中国、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南方,以及一些英国、法国、俄国前殖民地都存在过不同的奴隶制。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商品化程度较高。这和当时缺乏高度集中统一的奴隶主国家政权有关。美国的奴隶制建立在南部种植园农业基础上,奴隶们从事原料作物种植。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土地为国王所有,再逐级分封到各个奴隶主,奴隶和奴隶主是人身依附关系,但奴隶也有法律上的人格,虽不能和主人相比,但主人杀死奴隶仍然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而不像西方那样只看成一种对财产的侵犯行为。
各奴隶社会奴隶的来源有所不同。古希腊、古罗马等欧洲的奴隶一般来源于战俘、被占领地区原住民、负债者和罪犯,也有从非洲等地方拐卖到奴隶市场的人。美国奴隶的来源主要是英国殖民者奴役和贩卖的黑人。中国古代的奴隶多产生于战争,从敌方俘虏的平民成为奴隶,也有因犯罪被贬为奴隶的,有官奴和私属之分。在不同的奴隶社会,虽然奴隶的来源不尽相同,但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是其基本特征。
奴隶社会近乎残暴的压迫和极端不公的收入分配制度必然最终导致奴隶社会走向尽头。第一,在政治上,奴隶制度是一种不人道的制度。奴隶社会的残暴必然迫使无法像人一样生活的奴隶的强烈反抗。第二,奴隶主与奴隶阶级对立的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由于奴隶的劳动付出和分配所得缺少联系,奴隶的劳动积极性很低。奴隶主为防止奴隶偷懒不得不加强对奴隶的监督甚至惩罚,但这同样需耗费奴隶主的资源。奴隶为反抗奴隶主的强制劳动有可能选择破坏生产工具,这又导致奴隶主故意给奴隶使用粗笨不易破坏的生产工具,必然降低其劳动的效率。第三,如果存在着一种制度安排可使奴隶主和奴隶获得更多的劳动产品,就可能导致奴隶主和奴隶共同选择这种制度实现奴隶主和奴隶的双赢。
这一新制度就是地主-佃农体制。奴隶主把原来奴隶耕种的土地租给奴隶耕种,奴隶主向奴隶收取地租,这时奴隶主和奴隶的双赢就出现了:奴隶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因为缴纳完奴隶主的地租后剩余产品就归自己;奴隶主也不用再耗费大量资源监督奴隶劳动了,而且还可能因奴隶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从奴隶的劳动成果中分得的比以前更多。这时,奴隶主便改变了称呼,叫地主,与此同时,奴隶也改变了称呼,叫佃农。下面就中国的经验而言,讨论从奴隶制到地主-佃农体制的变迁。
在中国的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和耕牛的普遍使用,耕种水平和开荒能力大幅度提高。同时,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各奴隶主不断让其所拥有的农奴开垦土地,而且对所开垦的土地隐匿不报,据为私有。由于当时所采用的是“徭役”形式的赋税制度,农奴以在公田的劳役为税,私田是无税的,于是私田大增。之后,领主发现,农奴在公田里劳作比在私田里“有所匿其力也”。与其榨取公田里的劳役地租,不如把公田也充作私田,统一收取实物地租。统一收取实物地租的形式不仅使劳动者切实体会到了努力带来的收益,从而促使劳动者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而且土地拥有者也因土地的不断开垦和农奴积极性的提高而获取更多的利益。这样,私田不断增加,导致国家税收占全部农业产量的比重不断下降。于是,齐国齐桓公在公元前594年开始实行初税亩,即履亩而税,按田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税率为产量的10%。此时,领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农奴变为佃农,农奴制转变为地主-佃农体制。
另外,《管子》提出了一种制度安排叫“与之分货”,即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下,由地主和佃农按一定比例分别获取农产品,即用地租的形式规定二者的收入分配。《管子》认为,在旧的生产关系中,农业生产者由于不能确定其生产活动能得到的劳动成果,不会有自发的积极性。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人“不告之以时”,“不道之以事”,耕种者决不会主动去做。一旦实行“与之分货”的分配办法,佃农就会“审其分”,为了增加农产品总量,以使自己的收入数额增加,他们必然父子兄弟尽心从事生产劳动。
叶世昌(1979)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认为,“与之分货”就是“用封建地租剥削形式来代替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形式,这在当时有利于提高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
由于从奴隶制到地主-佃农体制是使奴隶主和奴隶获得双赢的制度变迁,因此这种制度变迁通常不需要通过暴力实现。就中国的经验而言,完全是一种和平的制度变迁,没有发生奴隶对奴隶主的暴力反抗,也没有发生民众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政权以实现制度变迁。奴隶反抗奴隶主以及奴隶主对奴隶反抗的镇压虽然也经常演化为血腥的方式,但这只是加大了奴隶制运行的成本从而构成制度变迁的原因,而非直接导致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家巴泽尔(Yoram Barzel,2000)认为,奴隶主监督奴隶劳动的成本和政府保护奴隶主对奴隶的财产权利的越来越高的费用,最终导致了奴隶制度的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