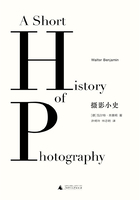
Ⅱ
要了解达盖尔照相术发明初期所造成的影响究竟有多么不同凡响,必须考虑到当时外光派绘画已开始在最先进的画家手中展现出全新的视野。阿拉戈深知正是在这个领域,摄影得向绘画接过承传的火炬,因此他在为波尔塔(Giovanni Battista Porta)的开创性物理实验成果所作的历史回顾中曾清楚地评论道:“关于大气不完全透明性所产生的效果(被不恰当地命名为‘空气透视法’),画家本身并不期待暗箱(指的是在暗箱内产生的影像之复制)能协助他准确地复制这种效果。”当达盖尔成功地固定住暗箱内的影像时,画家也在此分歧点与技匠分道扬镳。然而,摄影的真正受害者不是风景绘画,而是袖珍肖像画。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早在1840年,不计其数的袖珍肖像画师已多半改行,成了职业摄影师,起初只是兼差,不久便成为专职。(他们原来的职业经验对新的工作也有助益。)当时摄影的高品质表现并不是归功于他们的艺术基础,而是由于他们技术方面的掌握能力。转承期的这一代摄影家慢慢地消逝了,他们仿佛《圣经》世界的人物受到上天庇佑,得享天年长寿:纳达尔、史特尔兹内(Carl Ferdinand Stelzner)、皮尔松(Pierre Louis Pierson)、贝亚尔(Hippolyte Bayard)都活到九十近百。然而各地的商人终于争先恐后地进入摄影圈。等到底片修饰法渐渐普及后——这是恶劣的画家在向摄影报复——品位也急速降低了。而这也正是家庭相簿开始流行的时代。通常相簿是放在家里最冷落的一角,比如靠墙边的涡形脚桌或客房内的三脚桌上:多半是皮革装订加上令人厌恶的金属扣环、指头粗的切口涂金书页,里头排列着一张张人像,他们的穿着实在愚蠢可笑——阿列克斯叔叔与莉卡婶婶,格楚蒂小的时候,父亲刚上大学,还有我们自己,真令人羞愧至极:装扮成阿尔卑斯山民提洛尔人的模样,站在绘满针叶树的布幕前,吆喝着山歌,抖动着呢帽,要不然就是打扮成水手,倚着亮晶晶的柱杆站着,一腿伸直,一腿稍屈,好像非做这种姿势不可。这类肖像照使用的道具,如雕像的台座、小栏杆、椭圆小桌,提醒我们:那个时代的被拍者需要有个支撑点,以便在长时曝光的过程中保持固定不动。起初需要的只是头部扶持物或支架,不久从名画获得了灵感,为了满足“艺术性”的渴望,再添加了其他道具,比如第一个增添的是柱子和帘幕。到了1860年代,明智之士开始对这些画蛇添足之废物表示异议。当时有一份英国的专业报刊曾载:“绘画中的柱子看起来真实,可是摄影用柱子当道具却很荒唐,因为常见到柱子竟被直接立在地毯上。而大家都晓得,大理石或普通石柱是不可能建在地毯上的。”也是在当时,有一些相馆准备了布帘、棕榈树、壁毡和画架,放置在操作和表现两个区域的中间地带,又是刑牢房又是宝座殿。卡夫卡有张幼年的肖像照正可作为有力的证明。相片中的小男孩大约六岁,穿着又窄又小、令人几乎感到屈辱的童装,衬着过多的编带饰物,他站在一幅绘有温室冬园的风景画前面,棕榈枝叶僵立在背景中。甚至,就像为了使这虚假的热带景观显得更闷更热,被拍者的左手还拿着一顶宽边的大帽,如西班牙人戴的那种。若不是他那无尽忧伤的眼神想奋力主宰这个为他设计的风景,他势必会被布景吞没。

卡洛琳·史特尔兹内(Caroline Stelzner)
史特尔兹内 摄
1843年
这张影像,带着无限的哀愁,与早期相片恰成对比;早期相片中的人物并未像这名小男孩一般显得如此孤单伶仃,弃绝于世。早期的人相,有一道“灵光”(aura)环绕着他们,如一种灵媒物,潜入他们的眼神中,使他们有充实与安定感。这里,也可轻易地在技术方面找到对等的情况,因技术的基础就在于光影的绝对连续性,从最明亮的光持续不断渐进至最幽暗的黑影。这一点也能符合一条法则,即新技术的出现会将其前的技术推演至极限,所以旧有的肖像绘画在没落之前曾造成美柔汀(mezzotinto)法的兴盛一时。当然美柔汀法是一种复制技术,后来便与摄影的复制术结合运用。希尔的摄影作品如同美柔汀版一般,光线慢慢从黑影中挣扎而出。欧立克曾提到,因长时曝光的结果,“光的聚合形成早期相片的伟大气势”。而摄影发明初期同时代的德拉罗什(Hippolyte-Paul Delaroche)早已注意到这“前所未有”的印相过程,“如此纤巧,绝不会伤害色块的宁静”。具有“灵光”现象的摄影印相技术也是如此。尤其有些团体照留下了同聚一堂的幸福感,这种感觉仅在底片上短暂显现了片刻,旋又在“原版相片”中消失。就是这气韵之环,有时仍缭绕着已经过时的椭圆相框,美丽而适切。因此,摄影的这种初始形式常被误以为强调其中的“艺术完美性”与“高尚品位”。在拍摄这些相片的场所,对顾客而言,摄影师代表了新兴学派的技术师,而对摄影师而言,每一名顾客都是新兴崛起之社会阶层的一员,“灵光”栖息在他们身上,甚至深入到他们外衣的褶皱与领结的凹痕内。“灵光”并不只是得自原始相机的产物。当时被拍对象与技术彼此配合无间,契合程度至为精确,到了日后没落时期两者却完全背道而驰。不久,光学仪器的发展提供了足以完全征服黑暗的工具,能忠实反映自然现象。利用最明亮的镜头以压制黑暗,将“灵光”从相片中去除,正如同主张帝国主义的布尔乔亚阶级将“灵光”从现实中驱逐。可是从1880年起,摄影家却致力于模仿“灵光”,运用各种修饰伎俩,尤其是借助一种名为上胶(gomme bichromat)的技法来假造。因此幽暗的调子再度交织反映着人造的光影,蔚为风气,或至少这是当时的“青年风格”(Jugendstil)或“新艺术”(Art Nouveau)的偏好。然而,光影虽幽暗微弱,姿态却愈来愈明确刻意,表现出僵硬刻板的形式,更显露了这一代的摄影家在面对进步的科技时是多么无能为力。

卡夫卡童年肖像
本雅明自藏
拍摄者及拍摄时间不详
然而,摄影最具决定性的还是在于摄影家与其技术之间的关系。瑞赫特(Camille Recht)曾用一个美妙的比喻来说明这层关系,他写道:“小提琴家必须自己创造音调,要像闪电一般快速地找出音调,而钢琴家只要敲按琴键,音就响了。画家和摄影家都有一项工具可使用:画家的素描调色,对应的是小提琴家的塑音;摄影家则像钢琴家。同是采用一种受制于限定法则的机器,而小提琴并不受此限。没有一位如帕德鲁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的钢琴家能享有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同等的声誉,亦不能如后者展现出几近传奇的魔术技艺。”顺着这个比喻谈下去,摄影界倒也出了一位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那就是阿特热(Eugène Atget),两人都有高超的技艺,并且都是先驱人物。他们各在其艺术领域内有淋漓尽致的表现,无人可堪媲美,因为他们都具有最高度的准确性。甚至两人各自的抉择也很相近。阿特热原本是戏剧演员出身,因对演艺事业感到厌倦,放弃了舞台上的粉饰,从此去揭开现实的面具。他住在巴黎,穷困潦倒,默默无名。他将自己拍的相片送给欣赏的人,而这些人也都特立独行,与他不相上下。他不久前刚去世,留下了四千多张相片,经来自纽约的阿博特(Berenice Abbott)收集整理后,出了一本十分精美的摄影专集,由瑞赫特编辑出版。 阿特热在世时,新闻界“对他一无所知;他往往带着相片到四处画室兜售,每张只卖几分钱,通常只相当于一张明信片的价格,即那种风景明信片:表现城市的美丽景致,沉浸在湛蓝的夜色中,还有一轮修饰过的明月。阿特热对技术的掌握已登峰造极,可是这位大师终其一生活在阴影中,孜孜不倦地默默工作,却忘了在技术的顶峰插上他的旗帜;因此,不少后继者竟以为是他们发现了顶峰,不知阿特热老早之前已捷足先登”。事实上,阿特热的巴黎影像预示了超现实主义摄影的来临,为超现实主义有效布阵的唯一重要部队开了先路。摄影在没落时期,因墨守成规的肖像而乌烟瘴气,而阿特热出来打头阵进行消毒,净化了滞浊的空气,使一切重又清新明朗:他下手的头一个对象就是“灵光”-也就是近年来艺术摄影致力追求的价值-把实物对象从“灵光”中解放出来。前卫杂志如Bifur或《多彩多姿》(Variété)刊登了一些相片,配上地名作为图说:“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里尔”(Lille)、“安特卫普”(Antwerp)或“布雷斯劳”(Breslau)。相片中只见残断细节的影像,如一节栏杆,秃光的树顶,枯枝横现在一盏煤气灯前,石墙,灯架,以及一个救生圈,其上还写着城市的名字-这些相片只是将阿特热发掘的图式原原本本地指出来。阿特热寻找那些被遗忘、被忽略、被湮没的景物,因此他的影像正与那些城市之名所挑起的异国浪漫虚浮联想完全背道而驰;这些影像把现实中的“灵光”汲干,好像把积水汲出半沉的船一样。什么是“灵光”?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静歇在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截树枝,直到“此时此刻”成为显像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拉近事物-更亲近大众-现今已成为大快人心的趋势,正如同原仅独一存在的事物被复制进而被掌握,令人不亦乐乎。就近拥有事物,即拥有事物的影像或影像的再复制,已成为日益迫切的需求。然而新闻书报或时事影片中的复制影像显然有别于原来的像;与原像紧密关联的是独特性与持久性,复制影像则密切关系着短暂无常与复制性。让实物脱壳而出,破除“灵光”,标示了一种感知方式,能充分发挥平等的意义,而这种感知方式借着复制术也施用在独一存在的事物上。阿特热对于“美景和所谓的名胜地点”几乎总是从旁经过而已,但是他却会为了某些景象而驻足,比如排成长列的短靴,或从傍晚到次晨停歇在巴黎建筑中庭内的成排手拉车,或者杯盘狼藉的餐桌:这种景象大同小异,成千上百,同一时候到处可见;或者位于某街五号的妓院,门牌号码“5”大大地出现在墙上四个不同的地方。然而更奇特的是几乎所有的相片都空无人影。亚格伊门(Porte d'Accueil)旧城遗迹空荡无人,庭院,露天咖啡空无人影,帖特广场(Place du Tertre)渺无人迹,好似本该如此。这些地方不是荒废偏僻,而是了无生气:相片中的城市已经撤退一空,犹如尚未找到新屋主的房子。超现实主义摄影便是以这种潜能在环境与人之间安置了有益健康的距离,任由受过政治训练的凝视眼神在其中穿梭自如,在其注目之下,亲密家居生活的题材把空间让出来,留给了清晰显明的局部景物细节。
阿特热在世时,新闻界“对他一无所知;他往往带着相片到四处画室兜售,每张只卖几分钱,通常只相当于一张明信片的价格,即那种风景明信片:表现城市的美丽景致,沉浸在湛蓝的夜色中,还有一轮修饰过的明月。阿特热对技术的掌握已登峰造极,可是这位大师终其一生活在阴影中,孜孜不倦地默默工作,却忘了在技术的顶峰插上他的旗帜;因此,不少后继者竟以为是他们发现了顶峰,不知阿特热老早之前已捷足先登”。事实上,阿特热的巴黎影像预示了超现实主义摄影的来临,为超现实主义有效布阵的唯一重要部队开了先路。摄影在没落时期,因墨守成规的肖像而乌烟瘴气,而阿特热出来打头阵进行消毒,净化了滞浊的空气,使一切重又清新明朗:他下手的头一个对象就是“灵光”-也就是近年来艺术摄影致力追求的价值-把实物对象从“灵光”中解放出来。前卫杂志如Bifur或《多彩多姿》(Variété)刊登了一些相片,配上地名作为图说:“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里尔”(Lille)、“安特卫普”(Antwerp)或“布雷斯劳”(Breslau)。相片中只见残断细节的影像,如一节栏杆,秃光的树顶,枯枝横现在一盏煤气灯前,石墙,灯架,以及一个救生圈,其上还写着城市的名字-这些相片只是将阿特热发掘的图式原原本本地指出来。阿特热寻找那些被遗忘、被忽略、被湮没的景物,因此他的影像正与那些城市之名所挑起的异国浪漫虚浮联想完全背道而驰;这些影像把现实中的“灵光”汲干,好像把积水汲出半沉的船一样。什么是“灵光”?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静歇在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截树枝,直到“此时此刻”成为显像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拉近事物-更亲近大众-现今已成为大快人心的趋势,正如同原仅独一存在的事物被复制进而被掌握,令人不亦乐乎。就近拥有事物,即拥有事物的影像或影像的再复制,已成为日益迫切的需求。然而新闻书报或时事影片中的复制影像显然有别于原来的像;与原像紧密关联的是独特性与持久性,复制影像则密切关系着短暂无常与复制性。让实物脱壳而出,破除“灵光”,标示了一种感知方式,能充分发挥平等的意义,而这种感知方式借着复制术也施用在独一存在的事物上。阿特热对于“美景和所谓的名胜地点”几乎总是从旁经过而已,但是他却会为了某些景象而驻足,比如排成长列的短靴,或从傍晚到次晨停歇在巴黎建筑中庭内的成排手拉车,或者杯盘狼藉的餐桌:这种景象大同小异,成千上百,同一时候到处可见;或者位于某街五号的妓院,门牌号码“5”大大地出现在墙上四个不同的地方。然而更奇特的是几乎所有的相片都空无人影。亚格伊门(Porte d'Accueil)旧城遗迹空荡无人,庭院,露天咖啡空无人影,帖特广场(Place du Tertre)渺无人迹,好似本该如此。这些地方不是荒废偏僻,而是了无生气:相片中的城市已经撤退一空,犹如尚未找到新屋主的房子。超现实主义摄影便是以这种潜能在环境与人之间安置了有益健康的距离,任由受过政治训练的凝视眼神在其中穿梭自如,在其注目之下,亲密家居生活的题材把空间让出来,留给了清晰显明的局部景物细节。

莫贝街加尔莫修士市场(Marché des Carmes, Place Maubert)
阿特热 摄
1925年

卡伯莱,慕弗塔尔街
阿特热 摄
1900年

巴黎第五区布洛卡街41号中庭(Cour 41, rue Broca,5eParis)
阿特热 摄
1912年

位于凡尔赛的一间5号房屋(Maison à Versailles)
阿特热 摄
1921年

早晨六点的皮嘎勒街风景(Rue Pigalle, à 6h. du matin)
阿特热 摄
1925年

阿特热肖像
阿博特 摄
巴黎1927年

《摄影小史》第三部分首页 其中摄影插图为桑德(August Sander)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