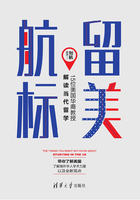
重拾“考证传统”绝非易事,学生要经得起批判
航:您当年从台大毕业一开始到牛津是否也有不适应,这期间有怎样的转变过程?
萧:我第一次跟我的导师杜德桥(Glen Dudbridge,著名英国汉学家)上课的时候,还有点懵懵懂懂不太了解。记得报到的时候,我高高兴兴地跑去跟他说:“老师,我已经把图书馆证件办好啦!”老师说:“很好哇,你要准备开始上课了吗?”因为牛津大学是一对一上课,不是大的班级上课。老师事先告诉你读什么、写什么,然后他对你交给他的东西进行辅导和评判。

英国汉学家Glen Dudbridge博士
航:就像带研究生吗?
萧:对,但它的大学(本科)部也是一样,都是个别辅导。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这种师徒传承的经验和教育制度经过多少代学者的实践检验,非常有效,美国这种方式就很难做到真正有效。但很不幸,放在今天来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这种方式有它们明显的缺点,就是学费太贵了。
回头再说我的老师,他见我刚来就兴高采烈地来见他,就拿了一篇文章给我,然后告诉我说:“下个礼拜读这篇。”那我就说:“下礼拜见。”因为当时还没有正式开学嘛,我就打算先回宿舍去。但当我下意识看了一眼老师拿给我的文章时,真是吓了一跳!那一篇文章是完全没有句号和逗号的《红楼复梦》的序。
于是我直接转头走向图书馆开始查典故,开始我也还不以为然,但到后来越细读越感觉脑门渗出汗来……原来这个序,虽然只有半页纸而已,但每一句话,都有两三个典故。你如果不查明白,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就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基本没干别的事情,把我所认为是典故的地方一个一个地查。但不幸还是有其中一句没查到,我现在还记得那句叫“两盈之间”。当时实在没看出来那是典故。到了上课的时间,我就按字面翻译把这句念了出来,结果被老师严厉批评了。老师说:“这是一个典故,你根本没有查到,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一个典故。”我闷着不说话,心里肯定也是委屈。但老师说:“去查!这是一个典故,我如果查得到,你一定可以查得到!”
好吧!我只能这样回去再认认真真地继续查。
时过境迁,我跟老师聊天,他告诉我,通常那一篇文章是他给研究生的下马威。大部分研究生拿到文章的反应就是:“哦,下礼拜才上课嘛,到时候带着这张纸出现就好了嘛。”这位研究了一辈子中国文化的英国绅士说我是第一个有点儿不一样的学生,能当时就意识到那篇文章有多难,有多少典故,然后回去认认真真做功课。
航:看来您那天虽然挨了批评,但其实给老师的第一印象还不错。
萧:至少老先生事后承认,他失去了一次给学生下马威的机会。我记得另外一次也是这样,某篇序里谈到一个词叫“胜国衣冠”。因为我不是中文系出身,古文功底没那么深厚,并不知道原来这个“胜国衣冠”不是表面上的意思。结果我就从字面上理解,觉得因为是“胜利”的胜嘛!就想说是当朝对不对?结果不是呀!原来“胜国衣冠”讲的是“前朝的衣冠”,于是又被老师严厉批评。老师直接说:“你看,都没有查,就来上课。”然后他就把一个字典丢给我。说你现在当面查!“胜国”是什么意思!结果一查……老先生说:“你看,你读中文,就不能够假设,你把前朝读成了当朝,怎么可能了解他真正的意思!”
航:看似只有一个字读错了,结果意思就完全反了。
萧:碰到这样的老师,我一段时间在阅读的时候,甚至已经失去了信心,看起来好像不见得是这个字面意思,那么就要赶紧查查看。现在看来,这就是必须要做到的阅读方式。古人就是这么读书的。“考据”,就是“字字句句”在证据上面来讲究。你要有很多逻辑上的思考才能决定到底是用哪一个字。
航:咱们现在太浮躁了,是吗?
萧:是这种治学态度和肯下功夫的精神现代人没有了。我很庆幸,自己当年在台湾没有碰到真正意义上的“考证学者”,结果到了英国,碰到了全世界“最后一位考证学者”,就是我的老师——Glen Dudbridge博士。然后在他的手下,我受到非常扎实的训练。他是心怀使命的那种人,不会顾及学生一时的心情好与不好。
航:您的博士学位能顺利通过,必然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萧:我还记得老师说我毕业口试的时候,他感觉是“我在考场里面考,他在外面考”,他认为如果我考不好,就表明他这个老师不够好。他还说他仔细回想过,从一开始我到牛津,到如今毕业,这中间整个学习过程,他都没见过我在办公室哭过。
我说:“没有,我在外面哭过。”
然后他就说,所有的研究生都在他的办公室里哭过,他就是为了让他的研究生对这些东西,一字一句都要很小心、很注意,他通常都会把学生骂得一塌糊涂。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被骂得当面掉眼泪的学生。
我说我记得呀!我记得您第一次骂我的时候,我出了您的办公室魂都丢了,都忘了我是在牛津。可是我经历过那一次以后,就发誓我不要再经历第二次。于是从此以后,在学习方面,我除了那一次的“胜国衣冠”以外,就真的是每一次都查得很清楚,就是不想再被骂一次。
航:杜德桥老师一直很严肃吗?
萧:生活中他很和蔼可亲,还记得那一次我跟他聊完,他确定我的论文通过了以后,说要请我吃饭。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在美国工作,是从美国回去(考试)的,并且那时候我已经跟我先生结婚了。
航:噢,之前还不大好意思问您的个人生活。
萧:这次宴请,我先生也一块儿去的。我的老师也把师母带来,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庆祝。在我们吃完晚饭要离开时,老师就跟我先生讲:“She takes criticism, like a mam.”(她经得起残酷的批判,像个男人一样。)
航:这算是对您的毕业评语。
萧:对,他认为我一个从亚洲来的弱女子,应该会被骂哭。结果我不但没有当他面哭过,也不会因为被他批判得一塌糊涂就放弃,越挫越勇,偏要做得更出色,于是他就说我像个男人一样。能够得到这样的评语,我认为这是对我最大的肯定。